1985年,五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开始尝试以自负盈亏的方式创办一份艺术的报纸——《中国美术报》这份官方系统中第一份美术报由此诞生,它在一段时间内始终是当时艺术领域内最先锋的艺术现象和最激烈的艺术问题被呈现的平台。
 广州双年展评委与艺术家合影
广州双年展评委与艺术家合影如果说这份报纸标志着大陆艺术家和评论者对艺术媒体运行特定经济模式探索的第一步的话,1992年召开首届广州双年展则进一步向我们展现了当代艺术体系的建构和转变:它试图通过艺术市场的建立来改变当代艺术的生存机制,并将艺术市场视为当代艺术获得一定社会合法性和存在空间的可行渠道。新旧转变之间,这次展览的意图也受到了激烈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无异于剥夺了“艺术”的纯洁性和独立性,让资本和市场“玷污”了艺术。官方与民间、制度与市场,艺术与资本,游走在冲突的两极中,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摸索着未来艺术体系的可能形态。
转变的当然不仅仅是艺术体制,还有当代艺术形式和风格本身。1991年,“新生代艺术展”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参与展览的艺术家大多毕业自中央美术学院,不同于以《中国美术报》为阵地的“八五新潮”对具社会和生命关怀的宏大主题的关注,新生代更倾向“近距离”的呈现:他们转向身边普通的人,事和场景,追求细微、平实的描述。同一时期,“车库艺术展”在上海发起组织,在经历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和80年代中后期的反传统浪潮后,这一批艺术家开始直面当下的、本土的经验,追求述说中国语境下社会与和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感受。
 新生代艺术展,王友身、周彦、庞磊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新生代艺术展,王友身、周彦、庞磊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王浩《广告牌》,在“新生代艺术展”中展出。作品用照相写实的手法描摹了一幅巨型海报和停靠在海报前的货车。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事实上,八、九十年代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东亚政治、文化和艺术急遽转变的时期:韩国结束了多年的军政府独裁开始逐渐与世界接触,日本在泡沫经济膨胀和破裂的震荡下沉浮,而中国台湾正处于“解严”后曲折而浩荡的社会重建阶段。1993年,李龙雨和金贤金策划的“整形春天”在韩国展出,展现了韩国艺术挑战旧有形式并努力寻求转变的意愿;同时期,年轻的日本艺术家走上银座街头,积极找寻艺术参与和艺术呈现的替代性空间……在这个时代,东亚各个地区艺术体制的建构有了最初的样貌,艺术主题和风格也出现了开拓性的探索。一幅兼具冲突与扭结的亚洲画卷由此呈现:商品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变革持续冲击着不同文化区域,并在差异化的社会语境中迸发出多重面貌的思想概念和艺术取径。
亚洲是什么?亚洲可能是什么?亚洲地理和政治概念建构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便不得不尝试抛弃模糊的、一般化认识,去挖掘亚洲图景看似“和谐”的表象之下种种“失调”和“失调”之中的某种回响。这正是由东亚地区德国歌德学院发起的策展项目“失调的和谐”之初衷:项目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策展人、艺术家和学者,共同探讨和挖掘“亚洲”或“东亚”在历史和当代多方面的意义,并以视觉艺术的形式进行诠释。从2012年开始,展览走过了首尔、广岛、台北,最后来到北京。北京展览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亚艺术受到特别关注:在那转折的年代,各个地区正遭遇怎样的震荡和新契机?我们该如何把握其中的艺术和思想动态,从而剖开那个时期的复杂肌理?在以视觉作品回应这些问题的同时,北京艺术机构中间美术馆也筹划了“策展人对话:从艺术史的视角回看八、九十年代的东亚”讲座,从策展人的视角向我们呈现转折年代的东亚艺术图景。
 策展人介绍
策展人介绍韩国:日常的复苏
随着1987年“6.29特别宣言”的发表,韩国走上了民主化和开放国门的道路,并迎来了灿烂的文化创作热潮。在金宣廷看来,1980年代是充满变化迹象的年代:
首先,在1987年政府放宽了海外出行限制后,公民有了接触国外艺术更宽阔和直接的渠道。在国外学习的艺术家和艺术学生急速增长,他们中一些人和韩国报纸和杂志合作,向国内传达海外艺术的信息。
而当韩国与世界相遇,公众对全球化和全球世界的关注日益增长时,艺术家中又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压力和渴望,即找寻并构建一种独特的“韩国”审美。该时期出现了将西方后现代理论、西方当代艺术潮流和韩国“传统”绘画结合的尝试,受到批评家Suh Sung-rok称赞的“后单色画”(post-Dansaekhwa)便是一个典例:在他看来,它融合了传统韩国美学与当代抽象艺术,可以视为韩国艺术后现代探索的典范。
 韩国单色画运动代表艺术家李康昭作品《无题》,1991年
韩国单色画运动代表艺术家李康昭作品《无题》,1991年与此同时,经过1980年代末的民主化运动后,政治化的“民众艺术”和纯粹“为艺术而艺术”这两大主导性艺术思想间的对立逐渐化解,全新的一代在艺术家中崭露头角:他们出生于1960年代,大多是20来岁的艺术学校毕业生。这批新生的力量已经具备艺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多重视角,他们活跃在酒吧、俱乐部,尝试租用这些日常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作品。不仅如此,相比起上一代艺术家,年轻一代往往抱着更开放的态度与非艺术领域内的人士合作,并积极汲取非传统的材料和资源——诸如装置,新技术,亚文化等。
在新生代的力量下,1990年代的韩国现代艺术出现了向日常生活的回归——艺术家的关注点从社会议题和政治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当代韩国急遽变化的每日景象,城市和日常经验成为艺术新的自觉的议题。1993年在首尔Dukwon美术馆举办的一场名为“整形春天”的展览便鲜明地体现了年轻艺术家与“民众艺术”和“现代主义”两大主流划界,并探寻新方向和新内容的意愿。大量以日常物品为创作材料,或力图呈现个体经验的艺术作品涌现:诸如李昢将装饰有闪亮珠子和亮片的鱼放置在无人看管的聚酯薄膜袋中,在博物馆内展览一条鱼缓慢腐烂的过程;曹德铉运用石墨、炭笔、LED灯、调光器、彩绘木结构玻璃制作出《女人的历史》,试图引现那些被现代历史洪流遗忘的韩国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经验也成为现代艺术日常转向下一个重要主题。Lee Dongi将米奇老鼠与阿童木结合并重组出一个名为“atomaus”的形象,以显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韩国现代历史中的巨大影响。
 李昢,《富丽堂皇》,1990年代。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李昢,《富丽堂皇》,1990年代。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曹德铉《女人的历史》,1990年代,观众将透过一个忽明忽暗的箱体观看身着韩服的女性。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Lee Dongi, Atomaus, 1993
Lee Dongi, Atomaus, 1993日本:艺术在街头
1980年代末,在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经济支持下,大量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日本被设立。“失调的和谐”日本展区所在的广岛市现代美术馆便建于1989年,是日本最早展示当代艺术的博物馆。神谷幸江提及,在泡沫经济的繁盛下,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县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展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艺术被频繁介绍到欧美,而国内的艺术机构也开始接纳日本当代艺术。
但在这艺术馆和艺术展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时代,东京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却颇有郁郁不得志之感:他们难以在美术馆找到容身之地(尤其在画廊和艺术馆租金高昂的东京),更不满于当时的艺术制度——没什么人看的展览,卖不掉的艺术作品究竟有什么意义?怎样让艺术获得更多人的重视和承认?这些艺术家将目光转向街头。
著名的“银座漫步艺术”(The Ginburart)由此诞生:1993年4月4日到4月18日间,34位年轻艺术家在“步行者天国”这一周末步行区进行了游击风格的展出和行为表演。“银座漫步艺术”的主要设想人和策划者中村政人曾在80年代末在韩国首尔接触了“MUSEUM”小组(这个小组曾组织许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和展览来挑战传统的艺术博物馆体系),他受到了首尔各类年轻艺术家工作室的鼓励和启发:为何不在画廊、博物馆这些传统体系之外寻求艺术展览的替代性空间?为何不主动为自己创造机会?正如我们所见,“银座漫步艺术”走出了画廊,开始有意识地将公共空间作为艺术生产和展览的场所,并带来了在日常生活的氛围下艺术家与公众交互的机会。
 “银座漫步艺术”,宇治野宗辉,行为表演,1993 年,摄影:中村政人,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银座漫步艺术”,宇治野宗辉,行为表演,1993 年,摄影:中村政人,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被展览的作品多种多样,展现出玩乐性、实验性或挑衅性的姿态:中村政人在银座的路边展示了一个钥匙孔形的金属雕塑,岩井成昭将小型声音装置放在银座地铁站的投币储藏柜中,会田诚则在一个画廊门前扮演成乞丐兜售自己的作品。颇值得玩味的是小沢刚发起的“茄子画廊”(Nasubi Gallery)项目,他将邮箱、水桶或木制牛奶盒的内壁涂白,使之成为一个可移动的小型画廊,同时雇佣了一些流浪者做这些画廊的“保安”或者说“导览者”。“茄子画廊”创作的初衷本是批判当时的“出租画廊”制度,但随后,这个小小平台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受到更大关注,直到今天,“茄子画廊”仍以不同形式持续邀请着不同艺术家参与。
 小沢刚,茄子画廊/牛奶箱,1993,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小沢刚,茄子画廊/牛奶箱,1993,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1994年的“新宿少年艺术”(Shinjuku Shonen Art)可视为“银座漫步艺术”的延续。中村政人同样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与上一次活动不同的是,本次项目有了更广泛的参与者,艺术家们也更多地使用了新兴的媒介——除了通过在街头分发传单来宣传和展览艺术创作外,艺术家还使用帽子中隐藏的摄像机进行拍摄,建立自己的广播站,或将数码照相机获得的影像材料储存到软盘杂志中。不变的是该项目与“银座漫步艺术”一脉相承的精神:在传统的画廊、艺术机构外找寻替代性的艺术空间,让艺术创作真正融入到公共和日常图景中——它将更具在地性、参与性和互动性。
 八谷和彦的行为表演,1994年,他使用了随身携带的摄像机、电讯发射器和录像机做现场记录。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八谷和彦的行为表演,1994年,他使用了随身携带的摄像机、电讯发射器和录像机做现场记录。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中国台湾:转折年代的流放者或幸存者
八、九十年代的台湾与韩国颇为相似:两个地区刚刚结束长时间的军事独裁,正处于急遽的社会开放和文化重建时期。然而回顾转折年代的台湾艺术史,黄建宏看到的是普遍性历史叙述和个体化历史叙述间的紧张。他注意到,当大多数评论者将“解严”背景下台湾出现的诸如“息壤”,“试爆子宫”等实验性艺术计划视为本土当代艺术的新开端时,部分艺术家却在创作中抱持一种“最后的创作”或“艺术的死亡”的心态:罗大佑在1984年出版《昨日遗书》后辗转至香港、美国,再未回到台湾;陈界仁于1988年决定停止所有艺术创作……在那被视为充满自由与希望的年代里,这些创作者却经历了激烈的怀疑、抵抗和挣扎。台湾艺术家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对当时的事件有何回应?为此,黄建宏谈论了陈界仁、苏育贤和张纹瑄三代艺术家的创作和创作心态,尝试以此呈现艺术家对八、九十年代台湾的感知与回溯。
1983年,23岁的陈界仁在台北西门町大街冒着被逮捕的风险,和朋友进行了一场约20分钟的行为艺术《机能丧失:第三号》,他如此解释这次行动:“(如果不)与戒严体制进行直接的碰撞,那我不可能真正‘看见’和‘认识’被戒严体制规训过的身体与行为模式,以及清理已内化至意识深处的戒严意识。”这次以身体探索戒严界限的行动成为台湾首次公共空间内的表演艺术,而“身体”本身也成为陈界仁发掘权力与规训下的个体生活处境的重要通道。在时代转折之时,面对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种种困惑,“身体”是他确认自我的一扇窗口。
 陈界仁,行为艺术《机能丧失:第三号》,1983,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陈界仁,行为艺术《机能丧失:第三号》,1983,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而在作品《沙哟娜拉,再见》中,苏育贤试图以绘画的方式再现和改编黄春明那部带有鲜明殖民情结烙印的同名小说。“重制”成为艺术家回顾台湾历史的关键词:它将过去的历史与生命的想象结合,让作品成为历史性空间的寓言之地。与苏育贤不同,张纹瑄则尝试以更游戏化的方式来重组历史的关系:《台湾史的结构》里,艺术家一面用报纸的形式重述80年代台湾政治的历史,另一面则以录像的方式记录了民间有关80年代灵异事件的回忆,在这里,官方色彩浓厚的政治史与80年代异色的民间想象相互映照,显现出台湾历史的延展和拧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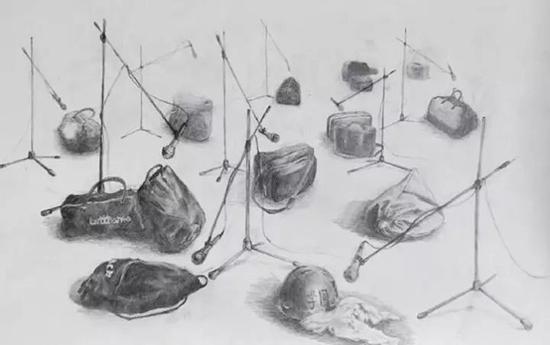 苏育贤,《沙哟娜拉,再见》,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苏育贤,《沙哟娜拉,再见》,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张纹瑄《台湾史的结构》,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
张纹瑄《台湾史的结构》,图片来源:中间美术馆在“失调和和谐”展览台湾部分,策展人选择以“前卫传说中的流放者或幸存者”作为该展区的主题。相比起对艺术家作为“开创者”、“变革者”的常见描述,“流放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窥看八、九十年代东亚艺术家心态和境况的不同视角:他们引入各种新概念、新价值,他们是时代浪潮前端探索文化工业力量与快感的先锋;但在同时,他们也试图在后殖民社会、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境况中进行抵抗、反思和跨越,并竭力挖掘和表现被主导性历史叙事淹没的、更为细腻而复杂的主体化状态。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