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驶入江户湾,强硬地打破了幕府闭关锁国的状态,也推动日本艺术沿着港口涌向了海洋的彼岸。陶瓷、珐琅、漆器、丝绸、浮世绘,这些充满东方风情的艺术品令很多西方艺术家倍感惊艳。凡·高一生都痴迷于收藏浮世绘,劳特雷克和莫奈等人也为之深深着迷。虽然这些巨匠大多一生都未曾踏足日本,却在多幅作品中留下了对日本艺术的喜爱与致敬。《日光西映:日本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就介绍了艺术史上这段震撼人心的东西方艺术邂逅。本文摘编自该书,由澎湃新闻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授权发布。
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为日本艺术打开了进入欧洲艺术界的关键之门。1869年,日本通过签署《友好贸易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与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1872年,日本与奥匈帝国签署的条约获得批准,这些都构成了日本参加世博会的契机。展会在多瑙河大都会维也纳举行:“维也纳普拉特公园开辟专门场地,250万平方米的建成区可容纳近40000名参展商。主楼是一座巨大的工业殿堂,有高达84米的圆形大厅和1千米长的旁路。东翼宽阔的长廊中正安放着日本国的展品。”
从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展厅的布置旨在更好展示日本艺术和手工艺,包括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作品以及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创作的物品。展厅规模宏大,设计富丽堂皇,垂着幔帐的房间装饰着皇室菊花图案,天花板上悬挂着彩色的大灯笼。展品包括巨大的瓷器花瓶、混凝纸制成的大佛头以及精确复制了镰仓大佛的铜头。展出的日本传统艺术品很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当代日本风味或专门针对欧洲人口味的作品。
这毫无疑问成为一场视觉盛宴,欧洲媒体热烈发声。不仅室内可以欣赏日本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室外也可以领略到日本风情。日式花园中包含了瀑布、小山、湖泊和桥梁,这些都是欧洲通过浮世绘彩色木刻所熟知的景象。奥地利皇室兴奋不已,因为组织者事先并未期望日本委员会如此关注细节。世博会开幕前,东京已经举行了彩排,以确保维也纳之行万无一失。前往维也纳的日本代表团有近80位成员,其中包括来自工业领域的工匠和专家、外交官和其他官员、口译以及顾问。此次日本参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纺织品到漆器几乎所有作品销售一空,约200种产品获得了奖章。
日本商品的市场在奥地利迅速形成:日本成为挂在每个人嘴边的话题,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商品,无论是茶叶罐还是和服,都变得炙手可热。新事物的美学及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为西方人带来了新理想,一种不受欧洲影响的古老文化竟可以通过其产品突然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这让每个人都为之着迷。
1873年世博会直接促成维也纳建立了一家东方博物馆。今天应用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中主要的日本藏品便是当年收购或捐赠的日本艺术品。博物馆原名为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Österreichischen Museums für Kunst und Industrie),当时共收到约50件物品,多为漆器和陶瓷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日本的视觉语言起到了表率作用,维也纳人热衷于购买日本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的营销策略得以实现:艺术品成为国家的大使,这项政策产生的效果空前成功。在那之后,日本政府屡次派遣技术观察员到世界各地进行访问,旨在了解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专长和与日本制造业相关的高质量工业产品,并自行创造。
当时的杰出画家,备受尊敬的巨幅画作大师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1840-1884年),同时也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老师,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日本热潮。维也纳世博会后两年,他创作了《日本女孩》(Die Japanerin)。这幅作品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带来令人愉悦的美感,画面描绘了一位艺伎风格装扮的维也纳女性,头戴发簪,手持扇子,穿着日式服装。“画家王子”马卡特过分夸张的风格尤其引人注目,画中人物的服装和花朵的排列都十分华丽。维也纳的日本主义可以认为是马卡特于1875年创立的。
与此同时,法国印象派画家也发现了日本:例如,1876年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在画自己的妻子卡米尔(Camille)时,为她穿上了日本服装。但与马卡特的画作一样,在莫奈的作品中,日本主义的影响在作品中仅起到了次要作用。莫奈的画作中,卡米尔身着日式长袍,装饰着立体刺绣,面朝观众,手持扇子,被画家本人视为失败的作品。然而,马卡特继续在他的画作中融入日式图案。

《穿和服的卡米尔》,1876年,布面油画,克劳德·莫奈,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法国人对日本的热情与奥地利人截然不同。在巴黎,德国出生的艺术品交易商西格弗莱德·宾成为日本主义在法国传播的重要中间人,使日本艺术品更易被同时代的人所接触。宾不仅是经销商,还是一位精明的出版商和市场战略专家,1888年,他创立了月刊《日本艺术》成为日本主义在法国传播的重要媒介。当凡·高踏入距自己住处仅几步之遥的西格弗莱德·宾的巴黎商店时,他对于日本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那时凡·高已经开始在安特卫普购买浮世绘木刻版画,并在巴黎继续自己的收藏。1887年他借鉴歌川广重的《开花的梅树》(Flowering Plum Tree)和《雨中的桥》(Bridge in the Rain),以及溪斋英泉(Keisai Eisen)的《花魁》(Oiran)中的图案进行创作,这些画作现存于阿姆斯特丹的凡·高美术馆。凡·高的作品与马卡特和莫奈有很大不同,日本艺术的直接影响在他的画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芝公园的寺庙入口》 (Temple portal in Shiba Park),1895年,粉彩,弗朗兹﹒霍亨伯格,私人收藏,维也纳
在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日本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风尚。事实上一群奥地利艺术家曾经前往这个国度,其中包括朱利叶斯·冯·布拉斯(Julius von Blaas)和弗朗兹·霍亨伯格(Franz Hohenberger),后者当时是维也纳分离派成员,后来成为领袖。但他们的作品和马卡特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持久的影响力。这些画家的肖像画和风景画都展现了日本及其现实的样貌,而非西方对该国度的浪漫臆想。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可以与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和男爵雷蒙德·斯蒂尔弗里德·冯·拉特尼兹(Raimund Stillfried von Rathenitz)早期关于日本的摄影作品进行比较。比托于1863年前往日本,并在横滨开设了一家摄影室,他拍摄的风格化场景从美学角度出发,获得成功,照片呈现出的真实的震撼力比后来奥地利画家的绘画作品生动得多。一个人是否必须亲自去过一个国家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这一问题还牵扯到其他画家和平面艺术家,诸如埃米尔·奥尔里克(Emil Orlik,曾游历日本,并将自己的见闻画了下来)和弗里茨·卡佩拉里(Fritz Capellari),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在1873—1903年这三十年间,出现了一些涉及日本主题的重要展览。
诗人和艺术历史学家埃恩斯特·舒尔(Ernst Schur)在《日本艺术精神》(The spirit of Japanese art)中用充满激情的字眼描述了日本艺术和文化:
日本人的艺术是一门极其沉默的艺术。当一位日本画家描绘具象场景时,画中人物似乎从不讲话,要么只发出一些流畅的音调,好像他们实际上在谈论其他事情。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种艺术能像日本艺术家的作品那样描绘出一种不活跃的存在。他们没有造物主,他们也不需要造物主使自己沉浸其中。他们可以立即消失,但他们已存在过,并将继续存在。因此,他们似乎总是全神贯注于自身,为自己的美丽而感到罪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给人们留下如此伤感的印象。
这门艺术的魅力之处在于它的绝对确定性。我们寻找统一性,这就是统一性,产生这种惊人效果的最深层原因在于自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自从我认识了日本画家,我总是为我们的颠沛流离而感到痛苦。我们似乎偏离了发展的道路,正无助地来回寻找一条迷失的道路。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想法控制了我们,以及我们与之相连的本能和欲望,生命中最黑暗的本质已经枯萎。从未有人逾越界限,在规则的边缘彼此掩护,一场痛苦又无畏的斗争开始了,日本人神秘出现,像主宰者一样,无所不能,从不失败,愿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力量是什么,愿他们的才华和天赋没有止境,永不枯竭,在他们所创造的物品中打上成就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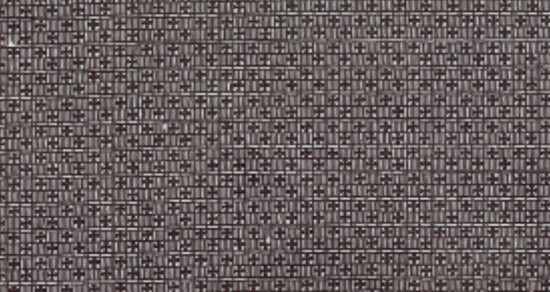
西博尔德收藏的型纸,应用艺术博物馆(MAK),维也纳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艺术家被日本艺术深深吸引,尤其是日本木刻版画上放弃透视的装饰性二维图案。图案的频繁重复指向一种永恒的艺术,它以完美对称的方式充分表达自己,这点尤其体现在19世纪末发现的大量日本型纸上(图4)。这种风格对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画家产生了显著影响,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20世纪60年代作品(图5)中的一系列对称物体就是这一概念的有力例证。

《夸特兰巴山》,1964年,布面金属漆,弗兰克·斯特拉,旧金山美术馆
斯特拉的早期作品如此,维克多·瓦萨雷(Victor Vasarely)或弗朗索瓦·莫雷莱(François Morellet)的光学艺术策略(图6)也同样适用。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非关系”的,因为它们超越了西方的作画方式。因此,日本主义并不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结,它是一段掷地有声的历史,需要深入研究,也可以说新艺术运动的发展尤其受到奥地利对日本主义态度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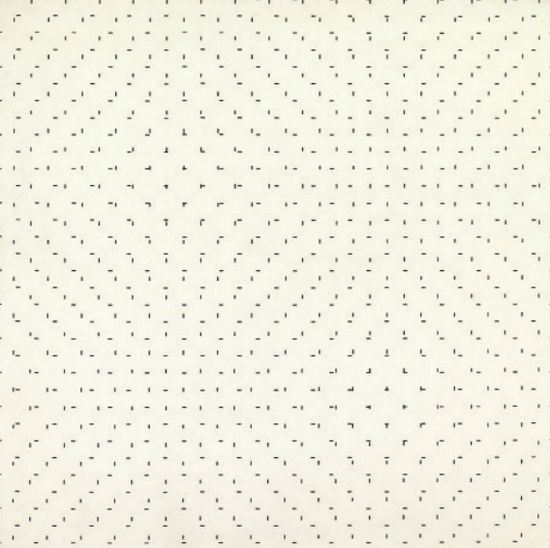
两幅条纹网格图,1972年,布面油画,弗朗索瓦·莫雷莱,彼得·史蒂文森的收藏(Peter Stuyvesant collection),瑞士
据加布里埃尔·法尔·贝克尔(Gabriele Fahr Becker)所说,20世纪初,维也纳对日本的接纳过程“涉及三个层面的需求:初创时代对充满异域风情的奢华感的需求;画家、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对未使用的形状和图案的接受度,目的是跨越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最终向往一种崭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在工业社会胁迫下发展起来的,并抵消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异化”。

《艾蒂儿﹒布洛赫-鲍尔肖像一号》,1907年,布面油画,添加金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直到2006年初都归上奥地利州的维也纳美景宫美术馆(Gallery Belvedere)所有,现存于纽约的新画廊(Neue Galerie)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尤其是他黄金时代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主义有很大的联系。让我们看看维也纳新艺术派的画像,一探其中的日本元素,尤其是1907年的《艾蒂儿·布洛赫-鲍尔肖像一号》(Adele Bloch-Bauer I,图7)。埃米尔﹒皮查恩斯(Emil Pirchans)在1956年这样描述道:
线条精妙呼应,膨胀、起伏、蜿蜒、颤抖、完美平衡,相互交织……他发明的熠熠生辉的珠宝装饰其中:方形、圆形、涡形、奇妙的图案、长长的准线、碎片和线条、匪夷所思的弯弓形状、星星、圆点、鳞状、网状、卷曲、扭动、颤抖的之字线、眼花缭乱并闪闪发光的水晶,就像雄鸡在斑斓变化的色彩中响亮的打鸣,金黄灿灿的色块是克里姆特的专属风格……
这幅画分为几个层次:左边区域几乎没有细节,被做成了马赛克状,而右边的人物是不对称的。作品受日本木刻版画设计布局的影响显而易见,女人的衣服和她周围的空间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结构,不易辨认。裙子上抽象的褶皱让人联想起日本美人图中的图案和形状。画中的女人似乎漂浮在宝座上,而金色的椅子乍一看是半透明的。画布底部区域再次突出了圣母玛利亚式人物的宝座。
克里姆特着迷于感性艺术,这部作品中的许多细节都透露出日本的重要影响。克里姆特曾数次提到自己的作品与日本艺术相关,他图书馆里的一些著作也证实了画家对日本的痴迷。
克里姆特还收集了中国作品和日本艺术品及手工艺品,在艾蒂儿·布洛赫-鲍尔的精美肖像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礼服的区域装饰着眼睛图案,这是古埃及真知之眼的符号。此外,我们还发现了方形、三角形、螺旋形和半圆形圆盘,克里姆特将其用于服装图案,为他的长期伴侣埃米莉·弗洛格(Emilie Floíge)作画。画家运用了大量的金色,表明他希望画中人物被描绘成一种神圣的存在。实际上中世纪艺术作品,尤其是背景中的金色,基本代表着神圣的世界,而且这些作品摒弃了其他绘画中常见的数学透视法。
克里姆特喜欢引用日本的美学传统:例如,在为1902年第14届维也纳分离主义展览而绘制的《贝多芬·弗里兹》(Beethoven Frieze)这幅作品中可以找到日本的家族徽章,也就是一个圆圈中有三个鱼鳞形状的图案。而圆圈里有一朵花这个日本图案则被他用在了1901年的作品《朱迪斯》(Judith)中。
克里姆特对这些非西方图案的使用纯粹是装饰性的,他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些图案的原始象征意义和用法。例如,在创作艾蒂儿·布洛赫-鲍尔这幅画时,左下角的条状物内随意使用了黑白棋盘图案,让人联想到日式榻榻米床垫的镶边,正是克里姆特把日本图案作为简单参照的例子。这种不拘小节的信手拈来让人联想起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尤其体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设计中。克里姆特显然把绘画对象的身体描绘成一个二维模式,因此欣赏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主体受到限制的感觉。虽然某些文学作品声称克里姆特是从浮世绘中吸取了这一特征,但关于这种可能性仍存在很多争议。克里姆特超越了日本传统,在这部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整体构图,而不是所谓的日本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图案非常复杂,但克里姆特并没有考虑它们最初的意义或用法以及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众所周知,漩涡象征着水流或升腾的蒸汽,克里姆特将其重新定义为情欲时刻,尤其在描绘画中人的头发时。克里姆特的绘画参考的是日本艺术,而不是日本人。

《秋风中飘动的树》(Autumn tree in moving air),1912年,布面油画,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立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维也纳
直到19世纪末,以汉斯·马卡特和他的同行们为代表的维也纳日本主义都在向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语言致敬,而日本则纯粹被视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主题。在克里姆特和埃贡·席勒的画作(图8)中,20世纪显然进入前景,成为重心,这是一种新的视觉语言,摒弃了传统的画面透视,形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空间张力。日本是这种艺术形式的起点,其通过新艺术运动获得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日本主义如何变化,都对西方艺术产生过催化作用。除了浮世绘传统木刻画的显著影响,1873年维也纳世博上首次亮相的明治时代三维作品的设计和主题也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奥地利艺术家。
![《日光西映:日本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英]格雷戈里·欧文 (Gregory Irvine)著,张晓美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2021年6月。](http://n.sinaimg.cn/fashion/crawl/300/w550h550/20210812/acc8-08c78654ad8b04173cac482c770ecb7c.jpg) 《日光西映:日本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英]格雷戈里·欧文 (Gregory Irvine)著,张晓美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2021年6月。
《日光西映:日本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英]格雷戈里·欧文 (Gregory Irvine)著,张晓美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书至美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