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上月底去首尔大学开研讨会,没想到会在韩国遇上埃及;在讨论国际冷战与艺术的圆桌会议上,也没有想到大半个世纪前北非与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相遇会给表面上看起来与其并无关联的研究带来何种新的视角。会议结束后,与两位学者一起去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德寿宫馆)参观,遇上这个极为重要的展览:《当艺术成为自由:埃及超现实主义者》(When Art Becomes Liberty: The Egyptian Surrealists(1938—1965))。美术馆所在的德寿宫石造殿西馆于1938年完工,据说是日本殖民时期韩国最早的近代石造西式建筑;本展览中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也是发生于1938年,是埃及民族主义与英国殖民主义相激荡的结果。这些当然是纯粹巧合,但也可以说是饶有意味的巧合,似乎可以象征着全球性的殖民主义与现代性相纠缠的文化现象。站在美术馆前面宽大的台阶上,仰望展览的巨幅海报,“艺术”与“自由”两个大字令我心生感慨:一部20世纪艺术史,“艺术”如何“成为自由”?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言,“以自由看待发展”,看待艺术更应如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1896一1966)在《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中说,“惟独‘自由’这个词还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我们承继了那么多的不幸,在这些不幸当中,应当承认我们拥有思想上最大的自由。”(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0页,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社社, 2010年)在时代的巨大不幸中,不应忘却的是“我们拥有思想上最大的自由”,这可能也是埃及超现实主义者所秉持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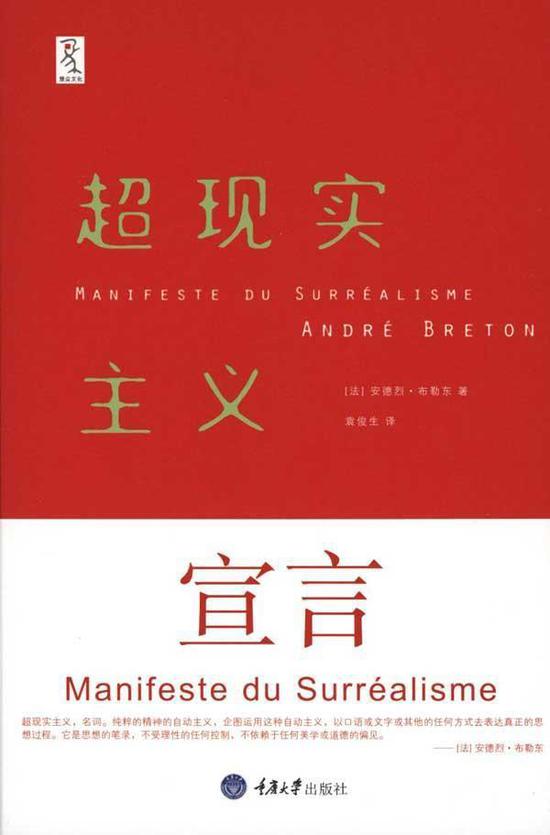 《超现实主义宣言》
《超现实主义宣言》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国际性,布勒东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没有祖国”,甚至是“作为超现实主义者,‘我们不爱自己的祖国’。”(《在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的演讲稿》,同上书,242页)因为他更为关心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他还一再提到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论述。但是他似乎很少对超现实主义是否应该或如何在国际漂移中建立更广泛的战线进行过正面的论述。1935年3月29 日在布拉格的一次演讲中,他高度评价布拉格的艺术家同行们的行动,“超现实主义运动应当为当前在布拉格所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他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超现实主义能够在国际上、在它所擅长的领域中成为权威。(261页)因为超现实主义“没有祖国”,因此他不会担心“谁之超现实主义?”;因为唯一酷爱的是自由,他必定会想象在什么地方、艺术如何“成为自由”。
20世纪埃及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20世纪的现代艺术现象中,全球视角和国际漂移以及与在地现实的融合中产生的艺术群体往往是现代性的历史脉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2015年11月康奈尔大学和开罗美国大学视觉文化计划(AUC)合作举办了一次题为“埃及超现实主义者全球视野”的国际研讨会,核心主题是从埃及超现实主义艺术看20世纪现代性艺术的全球关联,有些讨论议题即便光从题目上看也颇有意思:“埃及超现实主义的悲剧:个人见证”、“比较思考:其他超现实主义与全球表达”、“东方:可爱的猛禽与无辜之鸟——埃及超现实主义在东方/西方的辩论”、“埃及超现实主义者的政治议程:激进观点的问题与殖民语境下的世界性网络中的反斯大林主义等问题”、“抗拒现实:超现实主义在开罗与贝鲁特”、“合法防御:超现实主义、共产主义与在法国的不满”、“埃及现代艺术中的‘美丽的黑云’”、“埃及超现实主义的时光胶囊:卡迈勒·优素福作为见证人”……。很显然,这些讨论为20世纪全球视角的艺术史书写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这个题为“当艺术成为自由”的展览提供了学术基础。
该展览的主题是“探讨埃及超现实主义者的历史和演变,以及他们在埃及和国际超现实主义者圈子中的杰出遗产”。31位艺术家的160幅作品分为五个部分:一、全球视角下的埃及超现实主义,考察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开始及其对埃及的影响和蔓延;二、“艺术与自由”(1938-1945)作为领导埃及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群体,如何反抗剥夺艺术自由和压制情感的专制力量;三、埃及超现实主义与摄影,以凡萊奧的攝影艺术与技术探索为中心;四、关于“当代艺术小组”与埃及当代艺术运动的发展,其成员如何描绘当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五、埃及超现实主义(1965年至今)在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对埃及艺术的影响。在参观中,由于对埃及现代艺术完全没有研究,无法对于入选艺术家及其作品与埃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真实联系作出判断,更加无法透析作品背后的真实语境与作品本身的微妙关系,而只能从作品本身去感受作品所呈现的审美倾向、叙事主题及其与超现实主义精神的联系。
 《当艺术成为自由:埃及超现实主义者》展览
《当艺术成为自由:埃及超现实主义者》展览本展览图录《当艺术成为自由:埃及超现实主义者》(“When Art Becomes Liberty: The Egyptian Surrealists(1938—1965)”,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Korea,2017,韩英双语)收入了该馆策展人祖旺(Park Joowon)的《埃及超现实主义源流》(Traces of the Egyptian Surrealism)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哈桑(Salah M。 Hassan)的《当艺术成为自由:埃及的超现实主义者》(When Art Becomes Liberty: The Egyptian Surrealists ,1938一Present),这两篇论文分别从历史与群体活动的角度对埃及超现实主义艺术进行了深入论述。成立于1938年12月的艺术家群体“艺术与自由”聚集了埃及当时最重要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也有诗人、记者、教师和律师),他们以坚持艺术的自由权利、宣传自己的艺术主张、反抗政府对艺术的干预为己任,组织展览、出版杂志和书籍,直到1945年都很活跃,对埃及现代艺术产生重要影响。
尤为值得研究的是,在埃及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扮演了开创性角色的诗人乔治·赫内宁在1938年12月22日分别以法语和阿拉伯语发表了一篇题为“颓废艺术万岁!”的宣言,它断言艺术的普遍性,认为在宗教、性别、国家政治等问题上的不容异议以及妄图钳制艺术发展都是荒谬可笑的;有31位埃及知识分子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祖旺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必须注意的是这篇宣言中使用的“颓废艺术”这个概念,它显然与纳粹德国于1937年7月在慕尼黑举办的“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展”有很强的联系;而“颓废艺术展”是极权主义文化的标志性的邪恶象征,旨在使纳粹政府对现代主义艺术与想象的压迫制度化。(35页)众所周知,所谓的“颓废艺术”是德国纳粹政权强加于几乎所有现代艺术的标签,被纳粹批判的艺术家包括了梵·高、克里姆特、席勒、毕加索、保罗·克利、埃米尔·诺尔德等,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要把艺术强行纳入纳粹专制政治中去。被贴上“颓废”标签的现代艺术家被打成“颠覆国家的敌人”而遭遇迫害,作品被禁止展出甚至被销毁。但事与愿违的是,“颓废艺术展”竟然前后吸引了超过三百万参观者,是官方主办的“伟大的德国艺术展”参观人数的数倍。哈桑认为这份“颓废艺术万岁!”宣告了作为艺术团体的“艺术与自由”的诞生,它不仅成为现代埃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运动之一,而且其意义超出现代埃及艺术,同时也是国际性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及其国际艺术家圈子和批判知识分子的积极分支;他们发表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压制现代艺术的声明,反对强加于艺术的审查制度,相信艺术是“对于自由、力量和人类情感的极致表达。”(64页)他们把“保护艺术与文化自由”作为这个团体最首要的目标,坚持对法西斯专制主义和后来的威权政治的抵制,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超现实主义者和反对专制独裁的进步团体有广泛的联系。哈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艺术与自由”群体的崛起不仅具有激发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作用,而且影响了反殖民斗争,出现了“面包与自由”等团体。与“艺术与自由”群体不同的是,“面包与自由”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和公正等政治行动和问题。”(69页)
实际上,这就是埃及超现实主义使艺术“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与深远意义:它深受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与国际超现实主义圈子有广泛的联系,但是并没有脱离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没有脱离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些埃及本土的传统保守人士试图以“西化”作为攻击他们的理由就显得很无力。祖旺在他的论文中提到1939年在开罗的杂志上发表的保守派文章以及相关争论,当时Anwar Kamel 的回应是,“艺术与自由”群体毫无疑问更关注的是埃及而不是西方,因为埃及社会是一个失败的、病态的社会,已经失去了道德标准,并且陷入了经济危机;另外,Younan则认为虽然埃及超现实主义的确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但它是作为一个埃及的独立运动而存在的,与欧洲的趋势并非一途。(37页)
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以梁锡鸿、赵兽等画家为代表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34年)高举着经由日本传播而来的超现实主义的触目旗帜,一方面力图建构既独立、又与国际圈子同声同气的中国超现实主义艺术王国,另一方面同样不得不焦虑地关注和回应三十年代中国本土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与埃及超现实主义有点类似的是,他们也通过画展和创办刊物宣传自己的艺术主张,并且试图在广州与上海、东京之间建立更为稳固的现代主义艺术网络。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本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烈,中华美术独立协会很快自行解散,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彻底中断了它的存在。超现实主义在中国与埃及的不同际遇昭示着现代性的国际现象的复杂性和机遇性,但是无论如何,从非西方的视角研究国际性的现代主义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在艺术家的创作、宣言、团体之外,还有一种与艺术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主体性建构在国际漂移中存在与发展,那就是本土艺术作品在异域视野中的呈现过程;这也是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叙事中易于被忽视的议题,是观察艺术如何“成为自由”的另一种视角。捷克学者贝米沙的专著《布拉格的东方眼:捷克画家齐蒂尔研究》(周蓉、黄凌子译,广西美术出版社,北京画院学术丛书 ,2017年5月)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个案。沃伊捷赫·齐蒂尔(1896—1936)是一位捷克画家、美术教育家和收藏家,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时间定居中国,与中国艺术家齐白石等人过从甚密,收藏了大批齐氏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并且不遗余力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现代艺术。本书作者通过长期收集和精心整理的相关史料,从一个侧面勾画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艺术展览在欧洲的交流艺术史。
很值得重视的是该书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的比较另类的国际性视角,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一、通过齐蒂尔在中国的艺术经历而反映出来的20世纪初期西方在华画家的艺术创作与展览等状况,包括1919年由几位美国女性创办的“北京美术学院”这个“很有趣的组织”(18页);二、齐蒂尔在中国收藏艺术品的热情与在欧洲各地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览的巨大努力,既反映出他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敏感,也反映出他作为个人的局限性;三、刘海粟、徐悲鸿等人在二、三十年代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欧洲承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览,呈现了现代艺术在建构现代国家形象上的功能,而中国政府与艺术家在日本政府推广其现代艺术的刺激下所唤醒的国家身份认同则表明了现代性在文化竞争方面的重要性。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组织出国展览这个议题上的徐、刘之争,其中也能发现两位艺术家的所谓“世纪恩怨”中的偶发性的和国际性的因素。全书最后一部分是比较详细地介绍齐蒂尔收藏的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萧逊、邵锡濂、金城等画家的作品,其中关于齐白石作品的介绍份量尤重。透过齐蒂尔这只极具传奇色彩的“布拉格的东方眼”,我们看到的是另类的个人叙事与国际性叙事在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这又恰好是我们目前的主流叙事的框架与方法都有意无意地忽视的。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