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松
去英国泰特现代的涡轮大厅体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去香港维多利亚港“打卡”KAWS。这些原本在现实中、带着社交属性和在地意义的艺术作品如今在自家客厅也可以体验,而且仅需要一部手机。
这种体验依托AR(增强现实)技术,但是AR艺术程序与非艺术程序似乎差距不大,更像是大众艺术娱乐版。今年受到关注并有一定参与度,似乎还是依托艺术家的知名度,再以一种新奇的手段售卖其 IP产品。相比KAWS等大牌艺术家在技术上谨慎地尝试,更多以技术为主体的艺术家作品则更具前瞻性。最终,AR技术只是一种呈现“界面”,值得关注的还是艺术家的表达。

埃利亚松在他的AR应用程序中体验云技术
近几年,随着数字艺术的发展,艺术家、策展人越来越多地涉足数字领域,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全球大多数艺术机构不得不关闭,此时数字技术成为了艺术与生活连接的桥梁之一。如今运用在艺术领域“数字技术”主要包括XR(沉浸式扩展技术)、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MR(混合现实)。
相比XR、VR在展览作品或虚拟展厅中的运用,AR则直接在生活的周遭发生,其可以仅作为生活中参与艺术的社交游戏,也可以表达自己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再创作,且作为更广泛意义上公共艺术的一部分。

KAWS的“同伴”(扩展版)2020年
虚拟空间中,“打卡”明星艺术家的作品
一直以来,冰岛艺术家埃利亚松的艺术作品大自然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是埃利亚松的主要关注,他经常通过大型浸入式装置来探索,这些装置由艺术家对光线、湿度、材料等的敏感度精心营造和控制。因此,下载一款让人类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自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埃利亚松的工作的应用程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003年,埃利亚松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的《天气计划》
埃利亚松与伦敦的Acute Art公司(该公司生产和销售VR和AR技术)合作,推出了一款名为“Wunderkammer”的应用。更确切地说,这是将其过去作品与AR结合的“新作品”,不同的是,将走进美术馆沉浸式艺术装置化为生活中的即刻体验。在这件作品中,埃利亚松将太阳、云雨、海雀等自然现象和景观实验性地带入室内空间。
对于这件作品,艺术家本人解释道:在物理距离引导着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气氛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Wunderkammer的所有元素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有些是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我觉得它们应该被庆祝,就像它们实际上是奇迹一样。该系列中的其他元素将更具实验性,例如“光雕塑”和肉眼看不见的对象,除非你用手“抓住”它们。

埃利亚松作品的AR程序在生活中被运用
在AR艺术领域,埃利亚松并非首创,美国艺术家KAWS在3月初就借助Acute Art公司的技术将他标志性的作品“同伴”带到伦敦的千禧桥、纽约时代广场、东京涩谷十字路口等全球12个城市地标的上空,下载APP后就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带有KAWS玩偶元素的图像,不过如果想要在虚拟世界获得更多的“同伴”,就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付款。这种模式也让人想到2017年,法国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与Snapchat合作,允许社交媒体平台在世界任何地方创建其“气球狗”等代表性公共艺术装置,并鼓励全世界的年轻人用手机相机参与艺术创作,使艺术的体验民主化。

杰夫·昆斯与Snapchat的合作,依托地标虚拟生存其代表性作品
不同于以大牌艺术家为品牌的AR作品,今年7月,洛杉矶艺术家兼策展人南希·贝克·卡希尔(Nancy Baker Cahill)结合历史在美国多地开启了一个名为“钟”的AR结合3D动画的公共艺术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尽管作品是虚拟的,但想要体验需要到达现实中的地点,却又无需进入艺术机构的白盒子空间,作品也无需占据共享空间。

南希·贝克·卡希尔在自己的动画3D绘图被“捕获”,这也是“玩法”的一种。
据策划者描述,公众下载应用程序并到达某些指定观看区域,再将手机摄像头对准设定好的建筑对象,相关的动画便会出现,而在同一区域内的其他地点则只出现一堆五彩纸屑。
在纽约州,这件作品位于洛克威海滩以及附近四个单独地点。其中两个地点在手机屏幕上会出现铃声动画;另外两个地点提供了不同的红色,白色和蓝色波浪,在向海滨文化致意的同时,更提醒公众关注2012年桑迪飓风(当时摧毁的附近许多地区)和全球变暖的带来的危害。

纽约州洛克威海滩的虚拟AR装置,该站点提供了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涡流。
卡希尔对公共领域的AR作品并不陌生,早在2018年就协助策划在洛杉矶河上,涉及环境和移民等问题的AR艺术展览“定义线”(Defining Line),去年,她和杰西·达米亚尼(Jesse Damiani)在新奥尔良组织了一场AR表演“战场”(Battlegrounds),有24位当地艺术家加入其中,用AR作品与城市地点(受污染的水道、邦联的雕像等)和城市历史对话。
回顾过去,AR艺术在手机上的直接运用只是以艺术作品的滤镜效果达成自拍,而如今可以直接参与到动态的作品中,看似是一个飞跃,而事实上真是如此吗?与AR相系的艺术作品,与非艺术的AR应用程序是不是没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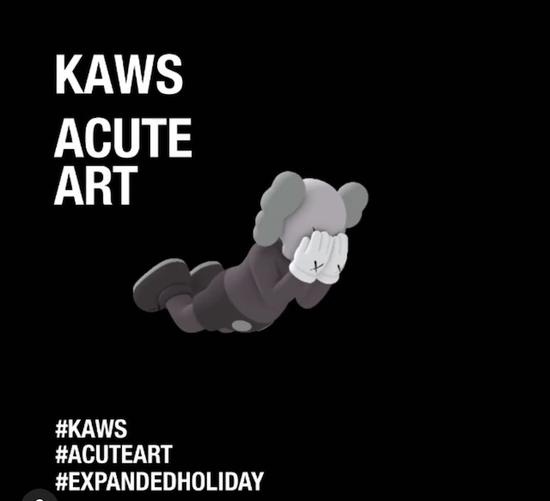
KAWS“玩伴”应用程序
AR只是一种“界面”,大牌艺术家只是在“售卖”IP
AR本是一种“滑溜”的介质,AR项目本身难于捉摸,它经常与VR(虚拟现实)相混淆,不同的是虚拟现实项目通常需要借助昂贵设备才能使用户沉浸在完全幻想的环境中,从而完全消除观看者自己的“真实”现实。AR则只要拥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就可以体验的增强项目;艺术家使用AR技术将创作预设在某个视野之上,再叠加到屏幕上真实。
对于AR艺术项目,惠特尼艺术博物馆新媒体策展人克里斯蒂安·保罗认为,“您可以使用AR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体验,而不必局限于某个机构。”
然而,在埃利亚松的应用程序中,公众可以如布置家具般,随心所欲地“安排”天气。厨房里可以有彩虹,孩子的头上可以停着 海雀,也可以在朋友不知情情况下在他的头顶飘过乌云,然后发布在社交网络上,整个看来像是一场游戏。在艺术中,这样的体验真的足矣?虚拟的“陪伴”会和现实的作品一样吗?回忆在实体空间感受埃利亚松的装置作品,也许同样也会有“拍照打卡发圈”的环节,但感受却相去甚远。

埃利亚松,矽藻窗户(Algae Window),2020年。玻璃球,钢,铝,塑料,黑色油漆。图为观众现场观看这件作品。
对于实体和虚拟艺术品的区别,在疫情期间一直被探讨,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他认为,技术会带来一种新的附加文化价值,甚至是新的文化形态,但是它和现实的体验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并且不是一回事。“在实体氛围中直接面对面地进行‘情感’交流,‘情感’是说不清,这就是虚拟和现实的不同。通过一个屏幕,无论技术如何强化,我可以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2016年,埃利亚松在凡尔赛宫举办展览,凡尔赛宫花园中轴线立起的“瀑布”
就实体作品和AR作品的区别,澎湃新闻也电话采访了目前还身处欧洲的策展人、艺术家李振华,他从1999年开始关注媒体艺术,也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媒体艺术的发展。在他看来,“在场性”是一种看作品的“界面”,“AR”是另一种“界面”。最终需要追问的还是艺术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期待的某种东西,到底是什么?
李振华也下载了KAWS的应用程序,他感受到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应用开发。而且很多用户下载软件、体验AR作品,首先是冲着艺术家的名气,比如KAWS的应用程序就是通过一个简约的、三维小图形(KAWS的“同伴”)的植入,相比真正意义上的AR艺术作品还有一定距离,更像是大众娱乐版。其整个逻辑还是依托艺术家的知名度,再以一种新奇的手段,来售卖 IP产品。而类似KAWS等大牌艺术家技术上所做的尝试是非常谨慎的,并没有走太远,只是在公众可接受、可被应用以及可售卖的范围内。

KAWS的应用“界面”
而就这些艺术家本身而言,现实中的艺术品和AR作品被似乎被设定为主体和非主体的区别,AR的扩延项目只是“扩延项目”,不是他们的主体性项目,比如,埃利亚松的作品的在场性体验中,能感受到他对空间和现场的把控,这是他艺术的主体,AR暂时还不能取代,或者说,因为今天的技术还达不到他们想要呈现的艺术形式。

埃利亚松使用自己的AR程序“控制”太阳
然而,AR等技术手段可以给任何一个空间贴标签,而不去干扰公共空间本身。艺术家或参与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任意地对公共空间进行入侵和改造,可是却不在现实中接入公共空间,这是技术手段带来的开放性,这种依托技术创建的对现实的注释,使其具有巨大的潜力。

AR程序中,杰夫·昆斯的兔子在埃菲尔铁塔草坪上
数字技术世界是过去和现在的集中体
AR艺术看似是近几年的产物,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最近开始备受关注,这种关注来自伴随数字时代成长的一代人,他们习惯通过社交媒体和手机看世界,并拍照与朋友分享体验。
当然,这种关注也来自于技术的革新,过去AR的界面识别中,需要依赖特别的软件或者识别码,可能还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而如今的AR作品几乎不需要依托实体空间,直接在智能手机上下载扩展软件就可以达成。
在深入探讨,李振华认为是技术界面的改变,因为手机等硬件技术手段的提升和核心算法的简化和图形化,带来的新技术的演化,使得当下AR作品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同时,相比过去绘制三维图形有非常繁琐的技术限制,如今简单的三维图形在iPad上就可以完成。硬件的完善和算法的简化,也让公众对改观了图形化的审美。而作为公众的一部分的艺术家也早已对技术不再陌生,为其使用或对抗技术提供了工作基础。

曹斐的《人民城寨》被认为是互联网艺术的早期开端之作
所以在能调动各种资源的“网红”艺术家之外,更多的艺术家很早就开始了数字艺术的思考和实践,只是公众对其的认识度不及KAWS等人,比如中国艺术家曹斐,2003年Linden Lab推出一款3D模拟现实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在这个游戏中,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虚拟的“第二人生”,并与这个虚拟世界的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实现自己在第一人生中没能实现的梦想。2007年,艺术家曹斐与《第二人生》合作,创作了《人民城寨》(RMB City),这是一件基于网络的社区媒体作品。在这座城市中,CCTV大楼、东方明珠、熊猫、烂尾楼和城中村分布其中,成为中国城市景观真实而又虚拟的映射。并延展出一个以真人构建虚拟世界的超大型作品。而相比10多年前依托三维游戏完成的艺术作品,近几年艺术家则融合多种技术,向MR领域探索,艺术家陆扬就利用数字技术创造了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却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活跃的数字人,将自己的脸、经过多年训练的舞者们所拥有的面部肌肉及身体肌肉控制能力、无性征的身体、精心设计过的纹身融合在了一起。未来这个数字人将伴随奇特变化夸张的视觉效果呈现于不同的数字平台,AR只是其作品的输出界面之一。

《陆扬数字人“独生独死”》(阶段性呈现)
在社交网络上,也有一些数字艺术家会发布一些未来世界的视觉作品,比如来自安特卫普的艺术家Frederik Heyman,他的艺术装置看上去像是平衡了时尚与艺术之间的空间,更多的是探索未来科技运用。“我热爱重现真实的世界,包括在各种交互关系和科技影响下的人类言行和情绪。我喜欢通过3D扫描的形式把自己的日常生活重新定位,把一些事物从现实生活中复制到艺术设计的领域,创建成另一个具象的物质。”Frederik Heyman说,“我觉得数字技术世界是过去和现在的集中体。”

Frederik Heyman为独立杂志《DUST》所制作的一组“大片”
此外,带给公众视觉未来世界体验的还有1980 年生于纽约的艺术家乔丹·沃尔夫森(Jordan Wolfson),他能熟练地运用动画、数字成像和动画电子雕塑技术,最近的作品以虚拟现实理念为中心, 将内心情感注入到自我构建的场景之中。2017年在上海西岸做过个展,他的最新创作中以经互联网搜索过滤的当代世界为出发点,以大型动画全息影像将投射一个当今世界非对称符号的重组,并对个体与媒介及接收信息系统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乔丹·沃尔夫森《江轮之歌》
相比早期的数字艺术作品,如今因为技术变化、界面简易,以及三维图形更简单地输出,让艺术家的作品通过手机就可以参与,在最新流行的一款APP“らくがきAR”中,自己在纸上的涂鸦也可以在手机中三维地动起来,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如今“界面”和技术的重要革新。这些革新为艺术家的作品借助智能手机普及提供了可能,其中科技公司在背后推动的功不可没。
虚拟世界也有法则,谁有权利传递信息,公众需要怎样的信息,怎样去抵抗虚拟世界中信息?个体有没有在虚拟世界逆向改变知识输出的架构的可能性?新的媒体和它的应用所带来的困境还需要时间去反思,而有的艺术家只是使用它,完成社会扩展。但无论如何,新技术的探索从未停歇,技术本身也一直在变革,人也在不断反思和反抗中帮助技术的完善。
附:
V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具体指的是利用电脑模拟三维空间,通过感官模拟一种沉浸感和临场感,就像把人带到一个虚拟的仿真世界。在美术馆中,已经常见通过VR眼睛程序的作品技术。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在真实空间里植入虚假内容,把虚拟信息(物体、图片、视频、声音等)映射在现实环境中。如果说,VR是带你精神穿越,AR则是高楼林立的现实中,再现海市蜃楼。
MR:混合现实(Mediated Reality),可以看作是VR/AR结合体,因为它指的是合并现实和虚拟世界后产生的新可视化环境。戴上MR设备,可见的人物可以跳出传统屏幕。
XR: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VR/AR/MR三者的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