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鹏特邀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石皓策划 /《中国美术报》艺术记者
为了纪念郎世宁诞辰330周年。7月16日,由中国美术报、中国艺术杂志社共同主办,中华雅集读书会、湖南创意读书会承办的“三百年的凝视——郎世宁绘画艺术”在北京二十四节气生活馆举行。特邀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张鹏,梳理与反思宫廷画家郎世宁绘画艺术的一生,先后从生平、绘画以及中西融合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诉诸。
郎世宁(Guiseppe Castiglione),生于意大利米兰。在十八世纪时,郎世宁以天主教修道士的身份入宫随即进入如意馆,正式成为了一名宫廷画家。他曾辅佐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其实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西方文化在中国开始流行,而当时在宫庭使用西洋器物数以万计就可说明西方文化受欢迎程度。郎世宁因此被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他一生主要以纪实性的方式为皇帝画了多幅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以及众多的人物肖像、走兽、花鸟画等作品。
在郎世宁的绘画生涯中,一直被士大夫长期诟病为“不中不西”,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绘画史上郎世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并且他将欧洲焦点透视法介绍到了中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学者。但是郎世宁却长期游离于艺术史之外,原因是中国艺术史主要以中国文人为主来撰述,而西方艺术史又对这个长期在异乡的画家了解甚少。近年来,在大陆、欧洲、香港拍卖市场上,为数不多的郎世宁真迹,均拍到了很高的价位。这也说明了一点,郎世宁开始被重新重视起来了。
 三百年的凝视——郎世宁绘画艺术 活动现场
三百年的凝视——郎世宁绘画艺术 活动现场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张鹏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张鹏传教士郎世宁的症结
在郎世宁的生平当中,他经历了一个以传教士的身份,不远万里从国外远渡到中国(他搭乘圣母希望号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于1714年4月11日启程远航。同行者还有擅长医药及外科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怀中。他们经过印度,于康熙54年(1715年)7月抵达澳门。依照当时传教士来中国的惯例,他们在澳门学习中文及生活礼节,以便日后与中国人士交往。郎世宁取中文名字郎石宁,稍晚称郎世宁。同年8月抵达广州。11月与罗怀中北上京师。)并进入中国宫廷这样一个特殊的个案,这中间其实混杂了很多问题。首先,他的这种多元化的背景与中国本土的矛盾,譬如传教士涉及到信仰与绘画职业之间的矛盾,以及在绘画上中西方文化在审美上的差异。这些都可以说是郎世宁一生中不可调和的症结所在。
明清以后,最早从西方以艺术家传教士身份进入中国不是从郎世宁开始的,而是被大家公认的利玛窦。据记载,利玛窦在万历28年(公元1600年),向皇帝敬献了一些西方带来的东西,其中就有一张耶稣的圣像,还有两张圣母像。这也是西方第一次以图像的形式进入本土的肇端。而此后,郎世宁才进入中国,这中间在时间节点上相隔110多年。
谈到西画,其实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认知,西方的审美其实是讲究对原物的复制,一种高度的模仿,就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非常逼真”,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面对中国当时的绘画语境,很多的文人画家、宫廷的画家其实都有一个很统一的审美体系,而且很完整与久远,而郎世宁所面对的是两种不同语境下的绘画形式,所以郎世宁一生都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牵扯着,徘徊着,中国艺术史是一个很残酷的淘汰史。他的严苛认可程度有着层层的审视与考核。所以能进入艺术史的人要经过谨慎的筛选,非常不容易。
其实,郎世宁的本意是以传教的方式来中国传播福音,但却进宫成为一名宫庭画家。当然郎世宁在欧洲也学习过绘画,曾为教堂绘制过一些神像。从这一点上看,传教士郎世宁其实有点不情愿的,但是无奈命运逆转,此后他在中国从事绘画50年左右,一直到病逝。乾隆皇帝一直倚重他,为他办最高规制的寿宴,赐寿礼甚丰,并亲笔书写了祝词。并且在传教案发生以后,他双膝跪地为教会高级人士向皇帝呈递奏折,向乾隆皇帝诉求,也并为引起天子之怒。乾隆只是温和地说:“朕并没谴责你们的宗教,朕只是禁止臣民皈依罢了。”
绘画生涯中的“西体中用”
女真族,历来有打猎的传统。公元1681年清帝康熙为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就有了“木兰秋狝”的仪式,皇帝每年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这里举行射猎,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郎世宁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地。在这里他画了很多帝王行猎的作品。譬如《乾隆皇帝落雁图》 《乾隆行猎图轴》《狩猎图》等等。乾隆时期,圆明园扩建工程,郎世宁也参与了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尤其是被人熟知的西洋楼,还有大水法12生肖兽头,也是他设计的。所以,郎世宁被称为建筑师,一点都不为过。
郎世宁的肖像画目前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因为绘制帝王的肖像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他画的大量的皇帝以及妃子、群臣肖像画中,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在造型上都非常严谨,注意解剖结构与立体感。譬如《高宗帝后像》《乾隆朝服像》。谈到这里,其实我们能看到他的很多帝后像都感觉很相似,其实这中间是有故事的。郎世宁写实画像一开始并不受欢迎,很多妃子并不满意,最后他殚精竭虑终于想出一个高招,先画一个标准像模版,然后稍加修改,绘成各人各自的画像,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平安春信图》
《平安春信图》谈到郎世宁的人物画,《平安春信图》是绕不过去的一幅。相比《百骏图》很大程度上西方油画的特质不是很明显,但是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勾线、平涂的人物画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这幅作品当中的山石、竹子的体积依然还是很立体的。这种立体的感觉,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绘画中是从来都没有的。这幅作品的特点除了有形式上的改变之外,还有更深刻的文化背景,胤禛、弘历穿汉装儒服,这时的弘历还是皇子,他们在竹园里拿着竹子,方桌上还象征性的摆放着如意,文玩以及一些食物。这种很和谐的父子关系,显然是郎世宁作为他者,进行纪实性创作的一种记录。这种写实的手法,进入了一种观念层面以后,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写实。所以,这里边有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含义:父子传承、文化传承。可以说是郎世宁作品风格转变的一件代表性作品。
 《乾隆皇帝大阅图》
《乾隆皇帝大阅图》相比明清以来,宫庭画家曾鲸、焦秉贞、冷枚都吸受了西画的方法,但是他们的主干仍然是中国画的传统,他只是学习了一部分西画的观念,以及对光影的塑造,比如烘染边沿的时候更加的有阴影,所以只能是一种对西画的学习与补充,因此我们称为“中体西用”,而郎世宁恰恰是“西体中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譬如《乾隆皇帝大阅图》,能明显的看出他有油画色彩的痕迹,但是它又运用了传统的工笔重彩,线描还没有抛却,主体的立体感很明显,所以这是我们把它归为“郎世宁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提起郎世宁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书画鉴定。目前郎世宁作品真假问题情况有三种,集体创作之后,没有郎世宁款;别人创作,落郎世宁款;还有一些盗名伪款;以及郎世宁画了一部分,其他人画了一部分,署名郎世宁款。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对他画作真伪鉴定的方向,同时也缺乏一些必要的研究。
 现场图片
现场图片 批评家 张瑞田
批评家 张瑞田 人民美术出版社期刊部负责人 王馨婕
人民美术出版社期刊部负责人 王馨婕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张新科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张新科 青年批评家 杜洪毅
青年批评家 杜洪毅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丁启阵(左起中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丁启阵(左起中间)中西艺术不可机械“融合”
明清以来,在中国画史上的中西融合是一个很大的现象。中西融合,是一个大而泛的词汇。晚清民国很多文人都认同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我们跟他处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那么在艺术史上,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在整个中西对话脉络中他应该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不仅仅是一个传教士为了生计而入宫,应该还有更多的关系,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亲历三百年中国画史,尤其是面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种逻辑方式在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中国除了被迫强制性的打开文明大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内化”的过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向清政府走私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我们才知道西方的器物文明,因此我们开始学习它们的制度、文化。其实这种历史观值得我们检讨,任何历史都是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势与弱势文化。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一直有一个“自我现代化”的模式,自我更新的内化模式。那么,这种内化的过程和郎世宁进入中国空间进行创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把美术史语境还原,回到乾隆时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画师聚集的地方如意馆,他们学习西洋的科技,那些文化创造,在当时这些人冷枚、唐岱、王致诚、艾启蒙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市场。他们每个人都在完成曾经有过的对于艺术的学习,他们在一起碰撞、交流、学习,而这个过程也决不是郎世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应该是一种交互的学习,这样我们的艺术史才能变得更加的丰富、更有趣味性。
最后在郎世宁个人探索上,对于我们中国画有什么启示?
中国画历来有“重神”思想,宋元之后,赵孟頫、苏轼,作为边缘的群体,他们有了主流话语权之后,就变成了主流绘画思想,反而那些宫廷画家被边缘化,那么又提到了顾恺之“重神论”,又沿袭到了郎世宁,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那么这种“重神论”,作为中国传统的审美,几乎困扰着郎世宁的一生。他想不想改变,或者改变中的困难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始终要面对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
中国文化的独立,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中西融合,到底能不能融合,哪些东西融合,都没有人进行细部的探究。文化的一体化,之前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强调在艺术上要追求世界艺术,那么就没有非洲艺术,也没有印度艺术等等,看似我们在追求普世的价值观,其实这种认识是有一定的误读的。中国画的存在不同于科技,全融,这些可能会全球化,但是文化不能,艺术没有任何全球化,统一的可能性,一旦统一化,就会被强势文化所吞噬。两种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模式。这个观念早在50年代,潘天寿就提到了中西艺术是两座高峰,或是两条河流,他可以两水分流,但是一定不能汇合,我们可以彼此遥望,看对方的伟大,或是相互学习,但是不能融合在一起。
郎世宁的一生可能经历过挣扎、复杂的心境,他的问题仍然没有完成,所以美术史上对他有“不中不西”的评价。其实不同文化母体之间,怎么融入到对方的文化里去,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不中不西”我认为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我们中国人去美国生活,你也许能融入他们的环境,但是你很难能融入他们的文化;再举一个例子,你在北方生活习惯了以后,你去江浙文人圈子,仍然很难融入其中。虽然在国内的学者对他的评价不高,但是起码在美术史上还是很重要的。他的“不中不西”恰恰是深度开阔的必要部分,这些其实对我们当代中国画是很重要的。
其实在画史类型上有两部分划分,一个是传统性,像齐白石、黄宾虹、吴昌硕等等。还有一部分是泛传统性,也就是中西结合,我们当代画坛很多人都是中西结合的画法。很多人学习素描、色彩,学习透视法,其实他们对中国传统笔墨没有向中国古人那样去深度了解。回过头来看,当下的画家学习画作,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表面上的一种交流,表面上吸取西方的东西。其实真正两种艺术的对话与交流,应该是深度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技法、形式、内容层面,你必须要对西方文化与西方艺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才能完成真正的创作。
所以20世纪,“中西融合”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所以郎世宁在中国文化融合的这一条道路上虽然未完成,但是他仍然有重要影响。
图书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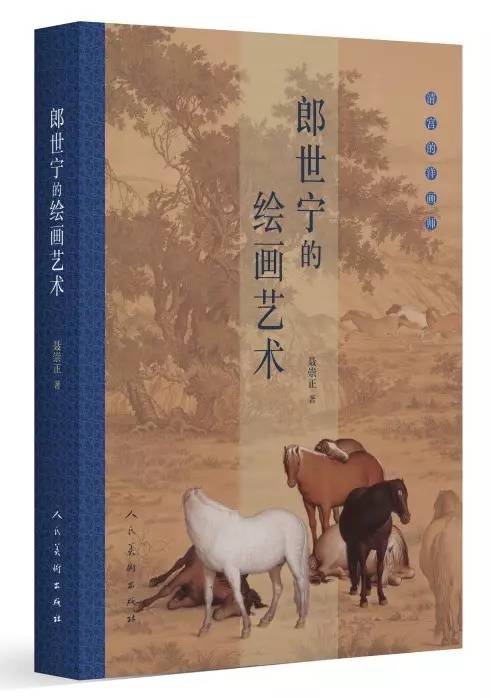 《郎世宁的绘画艺术》 作者:聂崇正 开本:16开 页码:228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郎世宁的绘画艺术》 作者:聂崇正 开本:16开 页码:228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