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使得现代人不读书了?冷漠了?肤浅了?肯尼思并不这么认为,甚至恰恰相反,网络和智能手机或许使得人类越来越好了。

按:2015年初,美国概念艺术家、网站编辑肯尼思·戈德史密斯(Kenneth Goldsmith)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了一门课——“在网上浪费时间”,学生上课使用的唯一教材就是笔记本电脑和WiFi,课程要求学生盯三个小时屏幕,仅仅用聊天工具、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互相交流。肯尼思·是这么介绍自己这门课程的:“……如果说点击、发信息、更新状态和四处浏览等行为,都是我们创作一部引人入胜而情感充沛的文学作品的原始素材,那又会如何呢?我们能否利用我们的Facebook来重写一部自传?我们能不能将网络重新构建成一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歌?这门以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作为唯一教材的课程,会将重点放在如何将漫无目的的上网行为巧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学创作……这门课规定学生必须分散注意力,进行多线程操作,并且要在网上毫无目的地肆意浏览。”结果可以想见,常青藤校园里这个专门教授如何浪费时间的课堂,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挤爆了。
在这门课上,肯尼思甚至还与学生一起列出了“在网上‘浪费’时间的101种方法”,比如:
在社交网站上删除一切你能删除的内容,除了删除好友和删除你的账户,计算一下,看看你的朋友之中谁删除的内容最多。许多人一起用 Skype 联系不在场的其他任何人,然后不要回答任何“你为什么这样做”之类的问题。在一个伙伴的社交网站账号中,找到他最早发布的消息,以及收到或回复这条消息的人。登录你自己的账号,将这条消息发送给这个人,然后和他聊一聊。删除你在社交网站上的个人简介头像,并尽可能长时间地让它保持空白。在网上找一首混搭音乐,像《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一样认真写出一篇关于它的评论。……
在《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书名里的“不”字被划掉了)这本书中,肯尼思不仅仅向我们分享了他的上课内容及方式,更重要的是,他针对一系列有关互联网、智能手机、Instagram和即时聊天工具的批判与偏见——比如“现代人不再阅读了”、“电子时代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全神贯注的能力”、“电子产品阻碍了我们的交流”、“过度沉迷于电脑会导致下一代混淆现实世界与假象”等等媒体主流观点——展开了批评和反击。肯尼思认为,这类耸人听闻的、充满怀旧情怀的文章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早在人们开始描述这一现象之前,科技就已经与大自然交织在一起了。“网络原本就是超现实的,是一个逻辑和荒谬的混合体,一种分散、自相矛盾的碎片化媒体。如果我们不是拼命想把这些碎片黏合为某种统一连贯的东西,而是走与之相反的方向,去探索、包容其分裂性,并由此凭借更为系统的方法去定义其本质——一种拒绝单一化的媒体——那情况又会如何呢?”
既然我们已走到数字化时代,再也离不开社交网络和电子产品,那不如索性放弃哀鸣和紧张,更加放松以及更加公正地重新看看这个世界、一起“沉迷”网络?
 美国概念艺术家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美国概念艺术家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让我们一起“沉迷”网络吧》
在网上浪费时间是指什么呢?很难说。我没想到竟然无法简单对它下定义。当我漫无目的地在网上点击时,是不是因为没有把这段时间花在工作上而浪费掉了呢?可我已经对着这个屏幕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而且说实话,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不去想工作的事情,开一会儿小差。但是,与我们对“在网上浪费时间”的一般认识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去看小猫的视频。好吧,也许我看了几段,但我真的对自己偶然点开的话题很感兴趣:总统、摇滚明星以及那艘军舰。当然,我可以不点开它们,但是我最终点开看,是因为我真的感兴趣。我没点开看的东西同样也有很多。如果你听信了网络专家的话,会觉得我们花整整三个小时看的都是“标题党”文章,也就是那些靠哗众取宠的标题哄你点进去的网页,这与我们在周六早上一坐下来就连看三个小时卡通片其实如出一辙。但事实上,大多数人上网时并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花三个小时。相反,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干很多事情,其中一些无关紧要,另一些则意义重大。我们坐在电脑前花的时间,是一段混杂的时间,它反映的是我们的渴望,这与两眼呆滞地坐在电视机前被灌输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恰恰相反,因为电视给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
网络使得现代人不读书了?冷漠了?肤浅了?NO!
这几天,我在网上读到的一些文章说“现代人不再阅读了”,颇具讽刺意味。当人们听说我在写诗的时候,往往会坦白他们现在什么都不读了。前几天,我在一家银行开户,那位银行职员听说了我现在干的事情后,叹了一口气,承认他最近确实读得比以前少了。我问他有没有Facebook账号,他说有。我又问他有没有Twitter账号,他说也有。我问他是否收发电子邮件,他说是的,每天都会收发很多封。我告诉他,那事实上他每天都在阅读和写作大量的内容。我们读的和写的东西,比过去30多年里还要多,只是读写的方式与过去不同了——我们是在略读、剖析、一扫而过、标记、转发、群发着语言,这些方式现在还未被认可为文学,但是随着一大批作者开始使用来自网络的原材料构建起他们的作品,这种新的读写内容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是迟早的事。
我经常读到一种说法:在电子屏幕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全神贯注的能力,变得很容易分心,无法聚精会神。但是环顾四周,我看见的却是人们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他们的电子设备,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全情投入的状态了。我发现,那些说我们注意力不再集中的人,往往也是最担心电子设备成瘾的人,这实在是很讽刺。同样讽刺的是,我发现我读到的大多数关于人们沉迷上网的文章,本身就来自网络,它们零散地分布在各种网站、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主页上。
在此类博客里,我读到了互联网如何让我们变得不善交际,以及我们如何失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但是每当我看见人们使用电子设备时,都会发现他们在互相沟通:发信息、聊语音、在线聊天。所以我难免感到困惑,这怎么就成了“不善交际”了?一段被割裂成许多短句和表情包的对话,仍属于同一段对话。看看那些正在你来我往、热火朝天地用短信聊天的人,他们脸上充满了普通人类的情绪表达——期待、大笑、感动。
批评者声称,仅仅是拥有电子产品这一行为本身,就阻碍了我们的交流,而治疗技术成瘾的最佳解药,则是回归最传统的、面对面的谈话方式。这些人说:“我们需要重新发挥交谈的作用。对于数字时代冷漠的人际关系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倾诉疗法’。”但是这种看法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智能手机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电话,它们都是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双向沟通的工具,且这种对话充满了情绪丰富的语音韵律与温存。难道在电话发明140余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在电话里的对话依然被看作一种缺乏“亲密感”的交流吗?并且由于以技术为媒介而被轻视吗?
人们都说,互联网让我们变得肤浅了。我们只是在浏览,而非阅读。我们已经丧失了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的能力。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我们会浏览和略读一些特定的内容,但对于另一些内容则会仔细精读。我们常常会把一些深度报道保存起来,等到离线的时候再拿出来读,也许是在下班乘班车回家的路上。那种批评的观点是假定我们所有人使用电子设备的方式都一模一样。但当我在地铁上从那些看电子设备入了迷的人背后看过去,发现很多人都在用手机读书、看报,虽然也有很多人在玩《糖果粉碎传奇》。

我最近看到过许多博客文章,都不遗余力地用照片记录人们在地铁上阅读纸质书的样子。其中一个摄影师用充满怀旧的语气表示,他想要捕捉一个渐行渐远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书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生气的iPad和Kindle电子书”。但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了,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简直像是单凭一本书的封面就判断它好不好一样。谁知道那些人正在读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用电子设备读书时,总会想当然地认为他读的是垃圾读物。有时确实是这样,但有时并非如此。昨天晚上当我走进客厅,我的妻子正对着她的iPad目不转睛,读着一本电子书:《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几个小时以后,我都要上床睡觉了,她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牢牢地被她21世纪的电子设备里那本171年前的传记所吸引着。当我跟她说晚安的时候,她甚至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
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不能不随新媒介改变
尽管那些评论三番五次地告诫我们,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已经改变了,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促使人们改变思考方式。如果在这场数字革命中,我们还像以前读书、看电视时那样使用大脑,那将多么奇怪呀!人们对互联网的抵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自从有了媒介,“文化反动派”就一直呼吁要维持当下的状况。马歇尔·麦克卢汉说道:“靠已有的知识和常规的智慧得到的利益,总是被新媒介超越和吞没……凡是习惯了传统媒介的人—无论他们习惯的是哪些媒介,都会把新型的媒介纳入‘伪’媒介的范畴,研究媒介的学者很快就对此见惯不惊、料想得到了。”
有人告诉我,孩子们陷入了巨大的危险:过度沉迷于电脑会导致我们的下一代混淆现实世界与假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分得清“真实”和“虚假”。我在Facebook上的生活,怎么就比我的现实生活更“不真实”呢?事实上,很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都来源于Facebook动态——工作机会、聚餐邀请,甚至是吃饭时讨论的话题,也都常常来自我在Facebook上看到的内容。况且,不少与我共进晚餐的朋友,很可能正是通过社交网络结识的。
……
这类文章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早在人们开始描述这一现象之前,科技就已经与大自然交织在一起了。法国的风景画家,例如克洛德·洛兰(1600~1682),就经常画一些被称作“理想风景画”的油画,将自然风光渲染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完美状态。于是,你会看到古典建筑的废墟在繁茂、稠密的丛林中若隐若现,可事实上,希腊那种多岩石的土壤中压根儿长不出这样的热带植被。这些画家声称,建筑是一种科技,要么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要么体现了自然被人类征服。就算身处亨利·戴维·梭罗那间位于瓦尔登湖畔的小屋里,你也无法逃离这间“隐士小屋”一公里外的东海岸铁路上传来的火车轰鸣声。
这份报纸上的另一篇文章也传达了同样的观点。这篇文章题为《放下手机》,重点关注了一些能够监控和限制你花在社交网站上的时间的软件。它最精彩的部分讲的是一个用塑料制成的智能手机模型,就是一块什么都干不了的塑料,但被吹捧成了“为那些想要摆脱‘手机瘾’,却因为出门不带手机而感到没有依靠的人提供的安全毛毯”。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中,“安全毛毯”是指一种同时代表着“我”和“非我”的过渡性物品。这个“同时作为‘我’和‘非我’”的定义,似乎更像是一个对我们的网络生活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评价,而非一场为了找回那个我们早已失去的、完整的“真实”自我而做出的声讨。在网上,我既是我,同时也不是我。那个“我”在Facebook上塑造的自己,当然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一个我希望在网络世界中展现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时很真实,有时却是一个复杂的谎言。
这篇文章引用了美国堪萨斯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的话作结,他不屑一顾地说:“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释放人类的两个基本欲望:我们既需要找到新奇好玩的事物来消遣,也渴望那种完成任务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句话总结了我们使用电子设备时的那种复杂的权衡举动。我们既具有生产力,完成着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又找到了新鲜有趣的娱乐方式。(“新鲜”和“有趣”什么时候变成反义词了?)正是这种反差(就好比酸甜口味的猪肉或是咸味的焦糖冰激凌)带来的刺激感,才使有互联网的生活充满了生机。这位教授还为一个事实感到惋惜:“有了这些电子设备以后,你每分钟可以获得许多次成就感。你的大脑确实被改造了,它进入了切换模式,不停地寻找着新事物,这使得放下手机变得十分艰难。”这在我听来简直太棒了。新事物和成就感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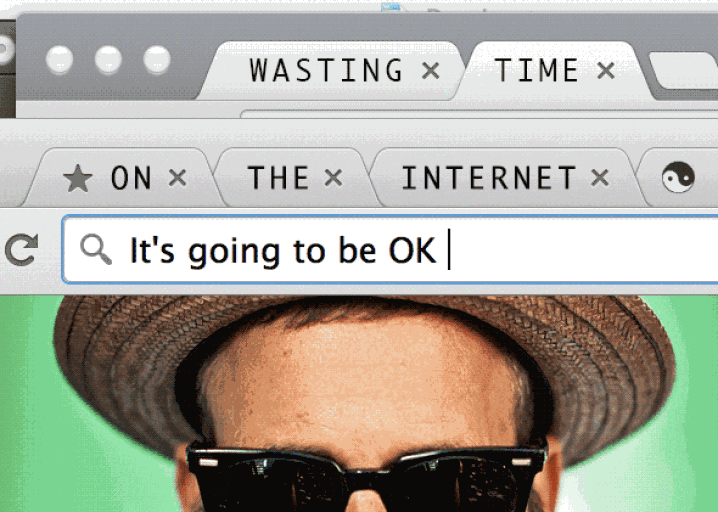 Facebook将成现代主义网络最伟大的集体自传
Facebook将成现代主义网络最伟大的集体自传网络,是一种被斯坦福大学教授西阿内·艾称为“蠢妙”的东西,即“愚蠢”与“绝妙”的结合体。BuzzFeed网站上那段小猫视频很蠢,可是作为其传播途径的Facebook却绝妙得令人称奇。反之,那段行车记录仪拍下的陨石撞击俄罗斯地表的视频,相当大气磅礴,可将它广泛传播的平台——Facebook——却显得乏味透顶。正是这种张力,使我们离不开网络。假如它只有愚蠢或只有庄重,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趣。网络原本就是超现实的,是一个逻辑和荒谬的混合体,一种分散、自相矛盾的碎片化媒体。如果我们不是拼命想把这些碎片黏合为某种统一连贯的东西(很多人都在不顾一切地做这件事),而是走与之相反的方向,去探索、包容其分裂性,并由此凭借更为系统的方法去定义其本质——一种拒绝单一化的媒体——那情况又会如何呢?
在承受了科技带来的巨大冲击后,现代主义欣然接受了20世纪鱼龙混杂的媒体格局及其所带来的破坏,并且声称这种混乱是其所处时代的标志。我并不是要过分沿用这个比喻(这是一个出现了新技术的新世纪),但是我们也许能从现代主义那燃烧殆尽的废墟中,找到一些有用的零星碎片,进而提取一些关于如何走进数字时代的线索。回顾过去,现代主义实验就像许多架在跑道上疾驰的飞机,其中包括立体主义飞机、超现实主义飞机、抽象表现主义飞机等,这些飞机逐个起飞、升空,然后很快摔了下来,紧随其后的是一次又一次中辍的起飞动作。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飞机根本没有坠毁,而是飞入了21世纪,并在数字时代里全速飞行着。假如说立体主义飞机赋予了我们将交互界面那零七碎八的外观理论化的工具,超现实主义飞机赋予了我们将神游和白日梦总结起来的理论框架,抽象表现主义飞机又为我们拥有的无处不在又一团乱麻的网络提供了隐喻,那又会如何呢?互联网闪电般的速度,为我们21世纪的美学提供了前进动力,这和一个世纪以前的未来主义者的诗歌,建立在工业的重击声和战争的警报声之上是一样的道理。
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见地。我们能否借由弗洛伊德对归档的看法来解释我们那疯狂的文件分享行为,或者借由他对意识系统的概念来解读ROM和RAM?我们能否将互联网想象成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1944年创作的短篇中描绘的那个无限的巴别图书馆的现实版?我们能否认为Twitter那种140字的限制,与海明威那篇精彩的一句话小说—“售:婴儿鞋,全新。”实际上一脉相承?约瑟夫·康奈尔的那些盒子装置艺术,能否被视为一种“前互联网”时代的、铺满图标与导航系统、仅有巴掌大的手持装置?《芬尼根守灵夜》是不是一大堆喷涌而出的话题标签?后现代主义的抽取与重新合成的行为(从卡拉OK到游戏再到嘻哈音乐,这两种行为在主流文化中十分盛行),也正是网络运行机制的基础。如果将互联网视作一台巨大的复印机,那么每一个从里面经过的人工制品,都会受到它那来回反弹的动作的影响(比如推文转发)。在这种情况下,人工制品的首要特征,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讲就是“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头,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而与此同时,它们仍然是承载内容的容器。
当未来主义诗人F.T。马里内蒂在1909年写下那句著名的宣言“我们要毁掉所有博物馆、图书馆和学院”时,没能预料到基于网络的文明结构将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艺术家接纳了以文化因子的短暂寿命作为一种新衡量单位的事实(考虑到短暂的集中精力时间是一种新的前卫标签),于是不再为永恒而创作,而仅仅创作出一些便于网络传播长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出现后的一瞬间就消失了,又被第二天出现的新作品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的每一个小动作都被搜索引擎存档了,并且被封存进了永远可调取的数据库中。与马里内蒂对擦除历史的呼吁不同,网络上的一切都永远存在。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巨型博物馆、图书馆和学院的综合体,包罗万象,囊括了从短小的状态更新到厚重的经典文本在内的所有内容。而你在网上浪费的时间、度过的每一刻,都在为它添砖加瓦,就连你的点击、点赞和“喜欢”也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透过文学视角来解读,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在网络上的停留,看作一篇篇毫不费力且毫无意识写下来的史诗,和凿刻在我们的浏览记录中的新记忆?此外,那个既辉煌又可怕的Facebook,可以说就是由文化所创造的一部最伟大的集体自传,未来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都将因它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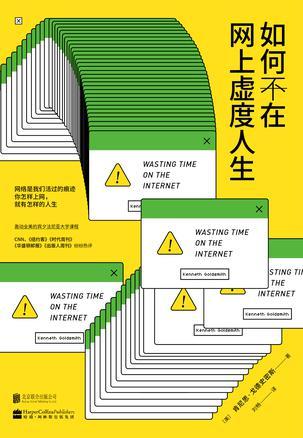 《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来源:新蓝网·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