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劳合- 费日(Laure Feugère)
原标题:完整丰富的唐代织品实例——关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纺织品
现存的敦煌出土丝织品主要收藏于中国、英国、印度、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众多研究和收藏机构。对于国外收藏的敦煌丝织品,总体只有零星刊布,罕见专门著作。中国丝绸博物馆从2006年开启《敦煌丝绸艺术全集》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出版的有《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俄藏卷)》。
本文原刊于《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主要介绍吉美博物馆的收藏品———多来自伯希和收集的纺织品,提供了更完整丰富的唐代纺织品实例。作者为法国吉美博物馆研究员,《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经中国丝绸博物馆授权刊发。

刺绣《佛说斋法清净经》片段 长:90.5cm;宽:27.8cm 唐代(7-9世纪) 此件绣品为敦煌藏经洞所出唯一的一件刺绣佛经。
1909年,伯希和从敦煌回到巴黎,除珍贵的手稿和画卷外他从中国获得的文物还包括一批珍贵的纺织品,如经帙、经巾、桌布和各色绢画等。绢画上的佛像常以银绘、墨绘或黄绘(石黄)为之,织物和石窟壁画中表现的相似。直到2010年,这批纺织品才最终得以全面清理和编目。
虽然是一手资料,但是伯希和对这些纺织品残片并不十分感兴趣,因为19世纪末以前中国还没有开始墓葬发掘。他在探险笔记中写道:“1908年3月7日,我发现两块奇怪的丝织物,一块是织物,另一块是刺绣,蓝色的绣地上用白色的丝线以锁绣针法绣以完整的《佛说斋法清净经》经文,字体非常奇特。”1908年3月13日写道:“今天找到一块罗织物,上面少数神像还非常完好。”3月20日写道:“一条精致的系带……”。但是关于纺织品我们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他的探险笔记花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手稿的发现。
1910年,伯希和带回的文物在其收藏地卢浮宫展出,其中可能也有一些纺织品,但是在沙畹的报告中没有记录。一些保存状态不好的幡被拆开来,只展出绘有图像的幡身,幡带等则长期丢在库房里。

吉美博物馆(图1)
一、克里希娜-里布
20世纪早期,吉美博物馆(图1)得到了不少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物。巾帙、系带和里面的经卷则在这批文物抵达巴黎时就已决定分给法国国家书馆。但是对这批纺织品的研究直到1964年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首席研究员让尼娜-奥布瓦耶委托克里希娜-里布(图2)担任伯希和收集敦煌纺织品研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1970年克里希娜-里布和里昂纺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维亚尔合作出版了《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纺织品》。

克里希娜-里布(1926-2000)(图二)
三十年来,里布夫人不但开启了对古代纺织品的研究,而且和她的先生一起慷慨资助吉美博物馆。1926年10月12日,里布夫人出生于加尔各答,她的父亲罗伊和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有血亲关系,所以因为父亲早逝,她从小就在泰戈尔家族的抚养下长大,在那里她受到了人本主义思想,印度文化重建和独立思想和全球性观念的熏陶。她曾就读于波士顿附近的韦尔斯利大学,到纽约后不久她嫁给了让-里布—一个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受驱逐而来美国。结婚后,他们在纽约的人际圈迅速扩大,很快就结识了诸如马克斯-恩斯特和亨利-卡帝尔布烈松一类的显赫人物。让-里布很快成为国际油田服务公司斯伦贝谢的总裁,里布夫人因此也得以给研究人员和艺术家提供帮助。
她常回印度看她的母亲,因此培养了她对印度艺术和传统文化的兴趣。她最早收集的纺织品就是家庭成员的纱丽,她对纱丽多样的制造工艺倍感兴趣。1962年,应马尔罗的提议,她在巴黎伯恩海姆-冉内画廊展出了她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纺织品,目的是帮助中印之战的受难者。这是里布夫人和让尼娜-奥布瓦耶的初次合作,后来正是后者委托克里希娜-里布研究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从中亚带回的纺织品。
通过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CIETA,Centre International d‘Etudedes Textiles Anciens)里布夫人认识并欣赏加布里埃尔-维亚尔,他们对东方纺织品织造技术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谋而同,认为这一部分鲜为人知,而在那之前对这部分的研究还属于艺术史研究的范畴。
1979年,因认同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让-里布帮助他的妻子克里希娜创立了亚洲纺织品研究整理协会(AEDTA,Association pour I’Etude et Ia Documentation des Textiles d′Asie)。该中心的一切都符合克里希娜的品味:设立在布勒特伊大街一栋古老的巴黎建筑的顶层,窗户朝向附近修道院的大花园,明媚、愉悦而僻静,研究人员和专家常在这里聆听来访学者讲学。克里希娜的藏品迅速增长到4000余件。
然而天不遂人愿,克里希娜随后遭受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重创,1985年让-里布不幸辞世,一年后,他们唯一的儿子克里斯托夫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然而,她却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AEDTA上。她和玛丽-伊莲娜-顾同领导下的一支团队共同致力于AEDTA的发展。她曾组织过一个名为《云彩之裳—日本袈裟》的大型展览展示日本纺织品。她出版过各式各样的画册并和该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合作出版过一些著作。
她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文,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她最喜欢的领域—汉代织锦。临终前她还购买了一些中国古代织金锦,因此开始探索织金锦和12-13世纪的契丹、女真以及吐蕃的联系。
在雅克-吉埃斯主编的《中亚艺术: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藏品》中克里希娜继续了对伯希和纺织品的研究,因为1970年出版的《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纺织品》以技术性研究为主,图片均为黑白,质量较差。直到这本书的出版,这些纺织品的颜色才得以示人。
少数几件纺织品在巴黎大皇宫1976年举行的《丝绸之路》展上展出过。里布夫人在韩百诗1977年出版的关于中亚的著作中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写道:“……这些公元前3世纪到唐代末年的织物的风格和技术等的演变和再现深刻影响着古代丝织的历史。”
2000年6月27日,里布夫人与世长辞。时值吉美博物馆正在装修,里布夫人临终前还看到吉美博物馆筹备的“里布展厅”,展厅将用于陈列她和丈夫捐赠的珠宝、艺术品和蒙古时期的印度织物。考虑到AEDTA可能很难再为她提供支持,里布夫人希望她的藏品和资料能入藏吉美博物馆。这个遗愿最终由她慷慨的后人黎北岚、托马斯和拉斐艾拉完成。
二、敦煌织物的展出
敦煌织物鲜有展出,在1976年巴黎大皇宫举行的《丝绸之路》展上也仅展出了其中的九件(包括团窠尖瓣对狮纹锦缘经帙EO.1199和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残片EO.1201)。

菱格纹绮地刺绣鸟衔花枝 EO。 1191/A 长: 8.0cm;宽:13.5cm 晚唐-五代(9-10世纪)

EO1191/A拼接图
1994年罗马举行的名为《丝绸之路》国际性展览上展出了三件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纺织品,除上述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外还包括一件鸟衔花枝刺绣残片(EO.1191/A)和一件鸟纹幡头(MG.24643),该幡头和其他六件非常相似的幡头都是由罗伯尔-热拉-贝扎尔重新整理的。
1992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名为《中国印象》的展览上又展出了两件,一件是联珠对兽纹锦缘经帙(EO.1207),另一件是竹编经帙(EO.1200)。后者还有蓝色和米色丝线编织的汉字“大智论第一帙”。
这些纺织品非常脆弱,不能长期展出,必须避光保存。我们得到这些织物的时候它们还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正是九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在避光、干燥的沙漠环境中的结果。而据斯坦因的记录藏经洞中也没有霉菌。
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纺织品大部分质地为丝绸,少数为麻布。幡画也主要绘在纤弱的单色织物上。但尤为珍贵的是衣服残片和不辞劳苦来回穿梭于中国、中亚、粟特、伊朗等地的朝圣者供养的织物。
三、敦煌与丝绸之物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枢纽,位于甘肃西端,在东西方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149年汉武帝确立敦煌为西部边陲四郡之一。汉以后,敦煌仍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莫高窟距敦煌城19公里,坐落在四面沙丘环绕的峡谷中,过去这里应该有许多寺院,现仍存有佛洞约469个。366年,据乐僔法师所见金光中山上有上千尊佛像。旅行者来此处祷告,供奉贡品,祈求神灵保佑他们远离旅途中的种种灾难。商队在旅途中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也频频来此处虔诚祈福。这种盛况持续了好多世纪,伯希和来访的时候还亲眼目睹了1908年3月6日的佛教庆典,成百上千的信徒来到此处朝拜。
426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敦煌继续发挥了边陲重镇的作用,唐代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
至吐蕃占领时期(781-847年),敦煌和中原的联系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848年,张议潮和敦煌豪族联手将吐蕃人驱离敦煌,发誓效忠朝廷,敦煌和中原的联系才有所恢复。这种局面维持了半个世纪,914年,曹氏家族取得对敦煌的统治权;公元847年,回鹘首领定都高昌,之后发展和保持了与敦煌的友好关系,至此东西两段都在两者的控制范围之内。9世纪情况开始逆转,中原和回鹘为争夺对敦煌的控制权征战不休,西夏对此地也是虎视眈眈,1036年藏经洞封闭就是受到西夏入侵威胁的结果。
现存敦煌纺织品并不只限于斯坦因(1907年)、伯希和(1909年)和奥登堡(1914-1915年)从敦煌收集带回国的部分(奥登堡收集的纺织品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数量约为伯希和的三分之一),还应包括东京和首尔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和敦煌莫高窟第130窟、122窟和127窟出土的六十余件8世纪的残品(大部分是用各色丝织物制作的长条状佛幡)。另外,在清理莫高窟第125窟和126窟前面的废弃物时还发现了一片487年的刺绣。
而近年来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青海都兰发现的织物则可视为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织造技术的重要实例。
陆柏认为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沿丝绸之路的贸易兴盛起来,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丝绸制作的幡在东土耳其和北印度的佛教庆典中已不可或缺。

文殊菩萨骑狮像幡 EO。 1398(P.196) 长: 81.5cm;宽: 18.2cm 中唐-晚唐(8世纪下半叶-9世纪)
这件残幡的幡手和幡足均已缺失,仅存花卉纹夹缬绢幡面和彩绘幡身。幡身面料使用画绢,上绘有结跏趺坐于狮子背上莲花座上的文殊菩萨,其左手持安慰印,右手持说法印。画面色彩仍旧鲜艳,特别是狮背上的联珠纹鞍体现了中亚织物的风格。

EO1398 花卉纹夹缬图案复原
据宋云描述,6世纪早期在于阗附近举行的佛教庆典上曾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佛幡,其中大半来自北魏。在舍卫城,丝质幡常作为供养物由朝圣者供奉给菩萨。
四、丝绸的重要性
过去认为丝绸能使人们与另一个世界沟通,所以,死者被包裹在丝绸里,像作茧自缚一样,其灵魂就可以升天。丝绸也加强了人间与天上的沟通,有时在供养和祭祀的时候以衣服或帛书的形式供奉给神灵。 例如,湖南出土的战国时期帛画《龙凤人物图》、《人物御龙图》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汉墓出土帛画都是为了帮助死者的灵魂升天。赵丰先生在尼斯举行的“天上人间—中国浙江丝绸文化展”上曾指出,这种将丝绸看作人和仙界沟通的媒介的思想源于殷商时期(公元前18-前11世纪)。
敦煌文书的研究使人们开始了解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日常生活和纺织品(主要是丝绸)在当地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童丕认为丝绸还曾用作通货,作用相当于古代的铜钱。早至汉代,政府就规定了纺织品的尺寸且价格稳定。5世纪出现一种宽56cm,长12m有余的纺织品,唐代依然沿用。赋税也可以纺织品的形式征收,以标准尺寸的色绢为主。丝绸并不是古代唯一可以用作通货的纺织品,麻布(包括大麻和苎麻)用得也很多。
纺织品的价值不仅由其材质决定还和织造技术有关。生绢常用来支付旅行中相关费用,色绢的使用非常频繁,过去官员的俸禄常以纺织品的形式发放,而在8世纪发放给官员俸禄中还未出现贵重的绮、绫和锦等。
745年政府发放布匹约15000屯匹给驻守敦煌的军队用以筹备粮草,除生绢、帛练外就是色织物,主要从洛阳和陕郡两大丝绸生产中心征集(敦煌文书P.3348(背))。
有些丝绸上附有官方印记标明其产地。吉美博物馆藏巨型绘画华严经经变画MG.26462(其一为《九会》,其二为《十地品》)的黄色缘边上有官印标明它出自“左藏库”。
在某些敦煌寺院的点检历中记录了少量与棉织物有关的信息。例如,9世纪使用的末禄绁(P.3432),但是这并不表示敦煌曾种植这种棉。麻是敦煌主要的纤维作物,和吐鲁番普遍种植棉花有所不同。在敦煌藏经洞就发现了一些麻织物残片。
唐时主要的服用纤维是大麻。丝绸主要产自北方,有时来自四川,苎麻产自沙州。在同一敦煌文书(P.3348(背))中记载了副使李景玉春夏两季禄为粟120硕,斗估32文铜钱,最后都折给了练。据童丕所言如果换成铜钱将会重达160公斤!童丕认为当时基本的货币是铜钱但流通中的却是丝绸。
童丕还指出唐和五代早期粮食的借贷(不管计不计利息)在敦煌经济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借贷的主要是丝绸,但也时有麻织物和毛织物。用于借贷的丝绸品质不一,即使是上好的丝绸也可按织造质量进一步划分等级。
幡多为绢质,大练(宽57cm)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幡画。据旧时的契约计算,绢在745年价值465个铜钱。敦煌文书P.2583记载936年紫绫的价格是绢的三倍,在敦煌文书P.2680中,绫则可以达到绢的四至七倍,还出现了一种“白花罗”,价格是本色绢的七倍。
五、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纺织品
从龙兴寺的点检历来看,敦煌的寺院会把那些根本不能使用了的残幡保留起来,或者因为它们的宗教价值,或者是因为它们曾用作法器,也或者纯粹是出于节约的目的。即使是很零碎的绫、锦和印花残片也得以利用。伯希和和斯坦因都指出,不能再使用的残幡被裁开继续使用在经帙、幡头、幡身或幡带上。供奉给寺院的贵重纺织品则常用作经帙、佛幡、帷幔或作为供桌桌布。
经帙

锦缘花卉纹绞经帙 EO.1209/I 长: 36.1cm;宽: 27.8cm 盛唐-中唐(8世纪)
佛经乃神圣之物,所以理应受到最高的礼遇—用非常珍贵的织物(例如缂丝)包裹或系缚。吉美博物馆藏有三件竹编经帙(EO.1200、EO.1208和EO.1209/I),风格独特,彩色的丝线与竹篾绞编,在经帙的表面形成花卉纹或几何纹。经帙的四缘曾用丝绸包边。
 红地联珠中窠对羊纹锦 EO.1203/E 长:5.4cm;宽:26.2cm 盛唐-中唐(8世纪)
红地联珠中窠对羊纹锦 EO.1203/E 长:5.4cm;宽:26.2cm 盛唐-中唐(8世纪)此锦属于典型的中亚风格斜纹纬锦织物,在深红色地上以绿、白、土黄等色纬线起花。织物外观呈梯形,保留下来的面积不大,可看到的图案为绿地联珠纹骨架中有一对相对而立的动物,四足,尾巴下垂,身上有两朵八瓣花纹样装饰。

EO1203E图案复原
经帙EO.1199上还明显残有这种缘边及用于缝合的米色丝线。从形状来看,纬锦残片EO.1193/A1-3、EO.1203/AA和EO.1203/E 似乎也是裁作经帙缘边。
里布夫人详细地研究了这些经帙。日本的正仓院和神护寺也收藏了一批经帙,制作非常精美的最胜王经帙上面还有纪年(752年),里布夫人将这两处的经帙进行了对比,最后发现使用竹篾和丝织物制作经帙其实是符合佛教精神的。
值得一提的是经帙EO.1208背面还糊有纸质文书,上有汉字且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有一张是令狐怀寂的告身,注明了他的官衔和姓名等。这种用写过的纸裱糊经帙的做法体现了僧人节俭的品性,纸在当时很昂贵,所以应该充分利用。童丕指出借贷契书常写在经文的背面(这种做法在阿斯塔那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有发现)。
经帙的形状视经卷的尺寸而定,宽度大约在27-32cm之间,自105年问世以来至唐纸张的宽度固定在24-25cm,所以经帙的宽度刚好适合当时纸质经卷的宽度。通常一帙十卷。
除竹编经帙外伯希和还收集了一部分纺织品制作的经帙,其中有一些反映了外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例如萨珊风格的联珠纹。
萨珊风格的联珠纹逐渐取代了汉以来的传统纹样。然而,有些纯粹的萨珊纹样,例如野猪头和伊朗的赛姆鲁却没有采纳,中国人相对还是更喜欢狮子、孔雀和翼马这样的题材。颈饰绶带嘴衔璎珞的鸟纹非常流行。
7世纪至8世纪早期是萨珊风格的鼎盛时期。在敦煌发现的织物中萨珊风格的织物只占十分之一,但在阿斯塔那出土的织物中却多达四分之一以上。
因为佛教纹样的符号化,佛教艺术对伊朗、中亚、拜占庭和印度风格的传入起了关键的作用。6世纪末萨珊风格联珠纹由粟特商队传入,常以动物纹为主周围装饰一圈联珠。粟特人对粟特纹和粟特纺织品(赞丹尼奇)的传入起了重要的作用。舍菲尔德和海宁认为布哈拉附近地区曾是重要的赞丹尼奇生产地。尚思教堂藏有一件粟特风格锦,其纹样和织造技术表明其与EO.1207、EO.1199(藏于吉美博物馆)和MAS.858(藏于大英博物馆)有很深的渊源。
EO.1199 和MAS.858几乎一模一样,和正仓院收藏的一件粟特风格锦也非常相似,织物结构相同,花纹为联珠对狮纹,非常漂亮,遗憾的是这些纹样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另一件经帙(EO.1207)上的纹样也是联珠纹但中间的动物已无法辨认。经帙上装饰缂丝带,优雅而华丽。
除以上两种,伯希和收集的经帙还有用其他材料制作的,例如草编经帙。
供桌桌布

绢画华严经变(图3-1 )
EO.1174是一块麻质供桌桌布,上绘对凤、对狮和一个镶嵌珠宝的香炉,周围装饰花边。类似的桌布在绘画作品里也有发现。绢画华严经变(MG.26462)中,每个佛像的前面都有一个覆以桌布的供桌,其上置香炉,桌布上的花边和这件上的非常相似(图3)。绢画EO.1250和MG.23076中观音脚下的供桌上也有同类的毯子。有趣的是同样的花卉纹样还出现在供养人衣服的袖缘上。

绢画华严经变中的供桌桌布(图3-2 )
幡
幡的数量较多,形状和材质也各异。据敦煌文书P.2613记载某寺院有幡大大小小多达380件,其中196件为绢质(其中24件为生绢),83件为麻质,五件为印花色织物。大部分为白色或本色,六件为浅橘红色,一件为红色(绫质)。
这些幡常有三种情况。第一种绘以菩萨;第二种为所谓的“错彩”幡,通常使用对比强烈的色彩,通过颜色的重叠获得一种类似金属的效果;第三种为银泥幡。在上述的幡中有102件属于第二种情况,83件为银泥幡。吉美博物馆也有几件幡使用了银泥工艺。幡或挂于旗杆,可随风飘扬,或作为一种供养具悬于峭壁。《大事》和玄奘所译《药师经》提到为除病消灾做仪轨要准备12多米高的大幡。类似的幡(有些已为残片)在藏经洞中也有发现。

花卉纹夹缬绢幡 MG.26460 长: 89.0cm;宽: 23.4cm 晚唐-五代(9-10世纪)
许多幡为“五色幡”,象征五方和五行。不同颜色的织物裁成大小相同的片从上到下一片接一片排列组成幡身。印花织物也常用作幡身。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幡有些幡身已经分离需要重新拼合,例如MG.26460在1910年抵达卢浮宫时曾纠结成一团,后来维亚尔和克里希娜都曾对其组合进行过研究。幡一般不一样,但是为了不浪费材料,僧人也喜欢制作大小不同的系列幡,所以才会出现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MAS.886)、吉美博物馆(EO。 1192/C1)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Д×202)的三个夹缬幡头竟然一模一样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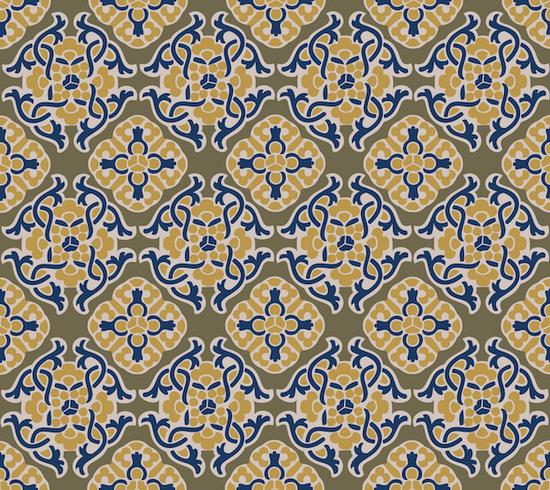
MG26460图案复原
幡头使用的材料一般和幡身不同。幡头斜边常用质地结实的锦制作,上有悬绊,可悬挂在朝圣列队手持旗杆的圆环上。许多一片式幡身绘有菩萨并装饰其他纹样。现存的幡很少保存完好,但是吉美博物馆至少收藏了十件保存相当完好的幡。
幡带
幡带的制作非常讲究。幡手缝在三角形幡头底边幡身两侧,与用来保持幡身平整的的细竹幡竿位于同一高度。有时在幡的背面可以看见细竹幡竿,常缠有彩色丝线,和华丽的幡身和幡带匹配。
幡身底部并排缝有三至五根幡带(又称幡足),底端相连并嵌入木质彩绘悬板顶端的凹槽。从伯希和收藏的几件幡足可以看出当时僧人的匠心独具。有些幡足上有菱格纹,有些幡足裁自同一片织物,两侧撬边。有些幡足的一边同时残有幅边,更加证实了它们是裁自同一片织物。有些幡足上装饰有墨绘纹样,如童子、祥云、山纹和花卉之类。
刺绣
刺绣少且多为残片,但有一个小型鸟纹幡头相对保存完好,针法为平绣。平绣出现在唐代,之前流行的是锁绣。自辽代起鸟衔花枝便是幡的常见主题。
麻
麻经常被用作幡面或幡衬,且大多数情况制作比较粗糙。
六、最近的工作
自1992年起对伯希和收集敦煌纺织品的修复一直在持续进行。敦煌的绢画曾用浅色丝绸镶边,但是1910年时,有些缘边被拆掉了,所以近年来克莱尔-伯尼奥夫人也在努力恢复藏品的原貌,例如,名为“42贤圣”的绢画(EO.1148)原来拆掉的红色缘边又重新装了回去,和画面匹配非常和谐。
对于那些1910年为了应付展览而拆开的幡,克莱尔-伯尼奥夫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清理和修复,基于此赵丰先生在这本书中才能得以全面研究这批织物和发表纤维的技术分析。
 银泥迦陵频迦纹绢幡 EO。 3585 长:197.0cm;宽:42.3cm 晚唐-五代(9-10世纪)
银泥迦陵频迦纹绢幡 EO。 3585 长:197.0cm;宽:42.3cm 晚唐-五代(9-10世纪)
莫高窟第12窟主室南壁迦陵频迦
此外,她还修复了一些幡带、悬板和丝织物残片。这些残片色彩各异,过去可能使用在帷幔上,和斯坦因带回伦敦和德里的那些残片类似。
虽然伯希和收集的纺织品不如斯坦因收集的那么精彩(当然,那些大型幡和竹编经帙还是相当精彩的),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完整丰富的唐代纺织品实例,使我们对唐代纺织品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图版和说明上,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虽然现在的研究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以往的认识,但是这批从遥远的唐代长安历经万水千山来到地中海岸的纺织品保存至今,举世无双,引起了全世界空前的关注和仰慕。
(本文鸣谢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图文资料,配图均为《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