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赴美交流展随想
 |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08 09
0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49 50
50 51
51 52
52 53
53 54
54 55
55 56
56 57
57 58
58 59
59 60
60 61
61 62
62 63
63 64
64 65
65 66
66 67
67 68
68 69
69 70
70 71
71 72
72 73
73 74
74 75
75 76
76 77
77 78
78 79
79 80
80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101
101 102
102 103
103 104
104 105
105 106
106 107
107 108
108 109
109 110
110 111
111 112
112 113
113 114
114 115
115 116
116 117
117 118
118 119
119 120
120 121
121 122
122 123
123 124
124 125
125 126
126 127
127 128
128 129
129 130
130 131
131 132
132 133
133 134
134 135
135 136
136 137
137 138
138 139
139 140
140 141
141 142
142 143
143 144
144 145
145 146
146 147
147 148
148 149
149 150
150 151
151 152
152 153
153 154
154 155
155 156
156 157
157 158
158 159
159 160
160 161
161 162
162 163
163 164
164 165
165 166
166 167
167 168
168 169
169 170
170 171
171 172
172 173
173 174
174 175
175 176
176 177
177 178
178 179
179 180
180 181
181 182
182 183
183 184
184 185
185 186
186 187
187 188
188 189
189 190
190 191
191 192
192 193
193 194
194 195
195 196
196 197
197 198
198 199
199 200
2002012年3月31日至4月17日,我随以中国人民大学郑晓华教授为团长的中国书法赴美交流展代表团作了18天的美国之游。由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新泽西州肯恩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书法赴美交流展成功的在肯恩大学举办,郑晓华教授为肯恩大学艺术系的师生作了题为《中国的书法》的精采讲演。之后,便是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使人难忘的采风了。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引发了同行书法界朋友们的许多所思,我将记忆中的三点与书法相关或引伸到书法的所思记录下来,成此三篇小文。
一厢情愿的书法走向世界
展览在肯恩大学高科技智能楼3D演讲厅展出,作品数量不多,尺幅都在四尺以内,与在国内的书法展览不相同,目的只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书法是什么样子,因为美国人多数不明白中国书法是怎么一回事。开幕并无国内大展的热闹场面,不设供官员排座次的主席台,在展厅中大家都站着,宾主各作了礼节性的致词之后,便开始对展览的作品参观,宾主双方三五人一群地对着作品交流。展厅的一侧备有自助午餐,有些来看展览的学生在展厅中匆匆走了一过之后,就直奔午餐而去,似乎这免费的午餐才是展览的主题。从老外的眼神举止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看懂中国书法,但又拘于礼节而在展厅中流连。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老外看书法只不过是看热闹而已。如同西方人看京剧,对各种各样的油彩画出的脸谱,对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舞台服饰和道具倍感兴趣,而对唱腔的细腻委婉、对情节的起伏宕荡并不太关心,也看不懂。对中国书法也是如此,他们对异于西方绘画的装裱形式,对笔墨淋漓如字如画的具有神秘感的篆书感兴趣,而对作品的传承流派、内在的审美境界则是一窍不通。展品有三件被美国人买去收藏了,其中有一幅是玉箸篆的对联,其实收藏者并不知道作品的优劣高下,他看上的是玉箸篆工艺化的技术及小篆结构装饰化的造型,作为一件奇特的工艺品来收藏。总之,老外对中国书法是“看热闹”,在高等学府的艺术系尚且如此!但这种书法交流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人虽然不懂中国书法所包含的深厚内涵,但知道了中国书法是个什么样子。
开幕下午,郑晓华教授向肯恩大学艺术系的师生们作了题为《中国的书法》的讲演。郑教授很博学,也很智慧,他的讲演大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存在价值及社会影响力;第二部分从中西方审美差异对比的角度,介绍中国书法的美学特征。他从社会和审美两方面向美国人推介中国书法艺术,而绕开了中国书法的流派传承、技法形式等具体内容。这些东西恐怕老外一时理解不了,反而会冲淡讲演的主题。讲演结束,听众与讲演者互动,美国人提出了一些大大出乎中国人意料的问题,如有一位美国人向郑教授提问:为什么书法都用黑色来写,而印章用红色?这个在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竟然使博学的郑教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就好像有人问为什么男人都剃短发而女人都留长发一样无法回答。老外提出的问题中国人觉得好生奇怪,但老外又觉得很有意思。这使我回想起多年前一位教授给我讲的类似的故事:他在讲课中对外国留学生们说,中国书法讲究力量的美,一点一画要有千钧之力,整幅作品要气势动人,颜真卿的书法就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之美。一位西方留学生站起来反问他说:老师,为什么书法只有力量才是美呢?无力就不美了吗?“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贵妃一定很美,就因为她无力的美而“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无力的书法为什么就不美呢?这是中国人万万想不到的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使这位教授一时语塞。看来,我们不能用中国人的尺度来度量老外的心思。
从肯恩大学到纽约,参观了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汉姆博物馆,后来又到华盛顿参观了国立美术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在波士顿又参观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又到旧金山参观了好莱坞的拍摄场地等等,此行在美国参观了十几个博物馆、美术馆,许多博物馆有亚洲展区甚至是中国艺术的展区,但遗憾的是基本上看不到汉字,更说不上有书法。而能看到汉字的地方,是美国各地唐人街上的店铺的繁体字招牌,和走进中国人开的中餐馆中墙上布置的“招财进宝”之类的民俗性的所谓书法。记忆中只有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看到吴昌硕的一块匾,上面刻着四个篆书“与古为徒”。白谦慎先生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作教授,他在二○○三年出版过一本不算厚的书《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的思考》,对书法经典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在国内书法界引发热议,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吴昌硕的这块匾作图版。如今我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匆匆之间也拍下了这张图片。(图1)吴昌硕在这四字篆书后的行书跋语中说:“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好古之心中外一致,由此推仁义道德亦岂有异哉!故摘此四字题之,安吉吴昌硕,时壬子秋杪客扈上。”读此知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应藏有甚多中国的书画名作,但却没有一幅作为中国的艺术品陈列出来。看来,仓硕老夫子的话说得不对,好古之心中外是不一致的,老外把中国书法只看作文字,他们把中国书法作品是作为文献资料收藏,而不是作为艺术品收藏。并且仓硕夫子所说的“仁义道德”的标准也不一致,中国人以龙为尊,以龙为德,而老外眼中的中国龙是凶残的猛兽,是神秘甚至带有邪恶的寓意。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在吴昌硕“与古为徒”的匾下就挂着一条张牙舞牙的铸铜的龙,(图2)对面布置了多条龙的雕塑。没有展出书法,却陈列着许多佛像,展出佛像的展馆灯光极暗,一束束射光打在一尊尊佛像上,使人有进入阴森的洞窟魔殿邪教般的恐怖,这是一些西方人眼中心中对东方文明的偏见,也是中西方文化的隔阂。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老外眼中的所谓中国书法与我们理解的书法艺术会是大不一样的。
比起西方欧美,在文化上日本是与中国较为相近的东方国家,书法篆刻艺术在日本很普及,他们的书法篆刻是由中国输入的,但许多日本的书法篆刻家及日本的书法篆刻爱好者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书法的文化内涵,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书法篆刻发生了适合日本人口味的形式化。例如日本当代的大书家村上三岛,他尊崇学习王铎的书法,成立了王铎显彰会,学王铎的“一笔草”。但与王铎草书相比,村上三岛的草书只是盘绕流动的线,而王铎草书则在流动中有顿挫的节奏,有着丰富的用笔变化,点画具有势态,有着“如冶出金、随意流走”的沉着痛快之妙。村上三岛学王铎草书徒具其形而抽空了内在的“质”,他并没有真正懂得王铎书中的庙堂气象及因人生经历而生发的情感在笔墨中的宣泄。又如日本的篆刻,强化了刀趣和章法的形式构成之美,讲求刀痕明朗、章法疏密对比强烈,但缺少了中国篆刻美的灵魂——金石气,所以日本篆刻有点木戳子的味道,像文字的版画,没有中国篆刻在形式变化中内在的渊古厚朴。我们的近邻、同时也是书法大国的日本,尚不懂得中国书法所追求的高格调及中国篆刻所表现的金石气,更无法希望西方欧美对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有什么深层的文化理解了。时下国内外办了不少国学院、孔子学院之类的教育机构,都开设了书法课,一些大学里也在教老外书法。但老外学书法只是依样画葫芦,他们只感受到用毛笔书写的新鲜与汉字结构造型的奇特,在学习中锻炼毛笔书写的能力,而并不懂中国书法是什么。孔子学院、国学院将气功、古琴、太极拳、书法并列为所谓的国学传统来推销给老外,一些老外在谈学书法的感受时,不是说毛笔书写技法的神奇,便是说书法有气功的作用,或者说字的结构像舞蹈的动作,而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书法他们并不懂得。
二○○九年九月三十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这是使书法篆刻界乃至国人欢欣鼓舞的一件喜事,当时的宣传强调了“书法篆刻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世界所认同并日益增长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确实是这样的,世界接受了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接受是有限的、肤浅的,仍需要经过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世界逐步真正认识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看一下当年一并列入名录的二十二个中国项目,就会明白外国人心目中对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定位,这些项目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舞、书法、篆刻、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端午节、妈祖信俗。”很明显,书法、篆刻列入这二十二个项目的行列之中,老外对书法、篆刻的定位同剪纸、甘肃花儿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民俗色彩的技艺,而不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定位,这与我们书法、篆刻人对这门艺术的认识定位相去甚远。
为向世界推介中国书法艺术,书法界作了许多努力,如中国书协举办“中国书法环球行”活动,有多个书家曾在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联合国总部等地举办书法展览和现场书法创作活动,这些对推动世界对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认知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真正做到“书法、篆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被世界所认同并且日益增长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恐怕不仅仅是这些举措所能独当的。尤其是有些书家在国外的书法表演,夸张了类乎杂技、气功的一面,为吸引老外的眼球而用了许多奇技和怪招,以书写者奇特的行头,“玄之又玄”的书写方式来糊弄洋人,这样一来,更加深了老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曲解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会。“书法走向世界”是个系统工程,只有中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强大,才会带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渐渐理解与正确理解。在世界对中国文化深刻而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真正具有了“书法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如果缺乏对书法篆刻艺术深刻的文化认知,一些书法人在国外使尽浑身解数眩人耳目的种种表演,在老外的眼中,就像我们看非洲土著黑人跳舞差不多,而且远不如黑人原生态的舞好看。
一切使“书法走向世界”的努力都是有益的、可敬的,但目前看来,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知不觉的书法走进当代
从波士顿到水牛城有名的大瀑布。在大瀑布边上看阳光下水雾形成的彩虹,被瀑布溅起的急风细雨弄湿了一身衣服之后,再折回华盛顿。这往返的路程都有七八百公里,我们一行所坐的大巴往返各走了整整一天。沿着美国北部邻近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两侧很少有出口,也见不到人影,路上的车子有序而高速地流动,并不拥挤。明净清澈的兰天白云,绵延数百公里不间断的森林,在阳光下透着娇嫩一望无际的草地上点缀着悠然的牧牛,这一切,使终日忙碌而终不知干了什么的我心绪一下子静了下来。在大巴士上眯着眼,让头脑木然起来,孩子在我的手机里输入了许多歌曲与器乐,平时也没听过,如今在这漫长而单调的长途行车中,戴上耳机听起音乐来。在这些平日里一直不以为然的流行歌曲里,竟然听出了些味道,而且渐渐随着音乐的旋律与节奏,身心与音乐共俯共仰。
对于流行歌曲,像我这个年龄大概都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开始听流行歌曲时,颇不习惯,觉得歌能么可以如此嬉皮笑脸地来唱,怎么可以手舞足蹈地来唱,怎么可以把手中的话筒扔来扔去,唱歌怎么可以像说话又像念经,絮絮叨叨像过去流传的“要饭调”?后来听得多了,慢慢感受到流行歌曲在旋律的明快与节奏的单调有一种一咏三叹的美,这种美与直白的民歌相通,又与《诗经》中不断重复的单一节奏息息相通。周围的人都在唱,流行音乐在电视广播中铺天盖地而来,自己也能跟着哼哼了。这其中有一个不知不觉被时风所感染并且渐渐同化融入的过程。
回忆一下自己唱歌的过程。四五岁时听妈妈在月光下吹洞箫,唱《苏武牧羊》,还有三十年代的老歌《渔光曲》,那时妈妈教我唱这类歌,六十年过去了,依然不能忘怀,依然能唱,那些歌曲是优美的、舒缓的、渊雅的,有着令人遐思的美境,没有说教,但能陶冶人的品质和格调。后来到了抗美援朝时,听着一卡车一卡车穿着宽大新军服满脸稚气、胸戴大红花将赴前线的新兵在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也跟着一起唱。三反五反时,学校让全校师生排成队,对着监狱后墙高高的铁棂子小窗,大家齐声高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拣,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那一条!”这些歌都是慷慨激昂的调子。再后来大跃进时期唱“党中央发布总路线,全国人民齐动员……”,“文化革命”时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再后来就是能唱得烂熟的八个样板戏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就这么一路唱了过来。改革开放起来了,突然听到异样的流行歌曲,自然会大吃一惊而不敢接受,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话题回到旅途中,继续在长途大巴车上戴着耳机听流行歌曲。听到一组称为“红色摇滚”的流行歌曲,都是些过去很熟悉,如今久违了,再来听甚至有点滑稽感的老歌,曲调、节奏、配器都流行歌曲化了,但歌调未变:“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公社就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歌词十分耳熟又十分遥远,过去曾熟悉的带有政治目的的严肃音乐一下子流行化、世俗化、娱乐化了,而歌词的内容是历史早已证明是错误的、早已废弃的词句,翻唱红色歌曲为摇滚,只是借尸还魂。如今翻唱这些歌曲,可视作是无歌词的歌曲,与龚琳娜无歌词甚至无语言的《忐忑》有相通之处。此类流行歌曲,一是突出了音乐的独立性、纯粹性,淡化或无视歌词“文以载道”的功能,不再成为临时的、具体的政治任务的服务工具,而是以音乐自身的美来服务社会、愉悦民众。二是旋律由激昂转为轻松,由政治性的严肃走向平民性、娱乐化、个性化,使歌曲变得可歌可咏、可亲可近、可舞可蹈,贴近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融入了当代社会大众之中。守旧如我者,也不知不觉地随着流行音乐走进了当代。
思绪又自然而然走进了书法。理一下当下书法三十余年走过的路,与歌曲的发展变化有着明显的相似。当下的书法,从美用合一走向了书法艺术的独立,从严肃与高雅走向了轻松与俚俗,由传统文人的小圈子走进了大社会,由精英文化演化为大众文化,古人视书法的“敬事”,今天的书法创作称“墨戏”,与歌曲一样表现出了平民化、娱乐化、个性化。书法从文人的书斋走进了展览会,由作品的独立赏读变为在众多作品对比之中形式美的凸现,书法的欣赏由传承的“读”变为“看”,这“读”是读其书兼读其文又兼读其人,而“看”则剥离剥了一切非艺术的因素,聚焦于书法作品的形式美。沈鹏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书法,在比较中索解》,文章站在当代艺术创作的立场,对书法艺术的本质作出深刻而独到的索解。他认为:书法是纯形式的,它的形式即内容,把书写的“素材”(文字内容)当作书法内容是一种误解,节奏美是诗歌与书法的共同特点,书法的历史本质上是书法风格发展史,书法不给人以知识,在文化的定位中,它只是一门艺术。这些论断明显是针对当代书法的艺术创作而言,也就是书法解脱了文字“用”的功能之后的特点。书法的“形式即内容”与上述“无歌词”流行歌曲可视为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类似的表现。而在古人眼中书法的界定是模糊的、多元的、包容的,是真善美合一的,是非纯艺术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学习书法的起步并不是在书法展览的环境之中的,经历了由书斋书法走向展览书法的过程,也是由不适应渐渐走向适应、再到主动求新求变,是一个渐渐融入当代的过程,并在融入中又成为推进当代创作发展变化的动力。
去年在《中国书法》工作时,编沈尹默书法专题。对沈先生的行草书创作,感觉尚能融入当下书法创作的审美,但对于他的临的魏碑等作品,就有隔了时代的遥远感。读沈先生的临帖之作,就如同我们如今再去听当年郭兰英规规矩矩对着话筒十分本色的唱《南泥湾》一样,没有声、光、电的喧染,没有一群伴舞者的烘托,也没有摇头扭腰的肢体语言配合,只有通过那本色的唱来表现音色美与旋律的美。沈先生的临帖作品力求结构的准确与点画的精美,笔笔到位,展示着深厚的动力,但没有也决不去想注入创作性的新变,这是那个时代书法创作的共性与主流特点。他的临帖作品许多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也就是距今七八十年前的作品,表现着当时文人书法的理念。我们读他的临帖之作,就如同读发了黄的老黑白照片,引起对往昔的回顾与眷恋。
我也喜爱临帖,如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可以使人入静。少年时临帖也写得很“实”。几十年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发生着变化,拿出几幅近年的临帖之作,忽然发现我也很“现代”了。这种“现代”并不是开始粗头乱服,开始老来狂,而是在临帖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下书法创作的理念,开始在形式表现上用心用意。数年前的一幅集秦官印印文篆书方幅,(图3)用宿墨,加手画朱砂界栏,印文间又加朱砂断句,在形式上颇为用心,可以说用新瓶装旧酒。其文字内容就如同唱红色摇滚“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一样全无意义,可视为无文字内容的书法,符合沈鹏先生“书法是纯形式的,他的形式即内容”的理念。再拎出几幅去年临的大幅作品,辛卯春节时如痴如醉地临写了一个月金文,此是其中的一幅,(图4)朱砂写主体字,墨书释文落款,朱墨相映,水色湮化,求在金文的古厚中表现自由书写的笔触,也就是在斑驳烂铜中加入时代的鲜活。另外两幅是去年夏天临写的敦煌残卷高适诗(图5)与选临汉《孔彪碑》(图6),虽为临古,选用了具有特殊装饰效果的纸,临与创已融为一体,有点像把过去正统的《南泥湾》、《社员都是向阳花》转化为如今的红色摇滚一样。
我本无意于现代,我的情性及能力也不具备现代艺术弄潮者的要求,但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现代。
权威与真诚的臭骂
由旧金山乘美国联合航空的班机返回北京需要十二个小时。机上的空姐不像中国航班都是佼好小姐,而是一色的半老徐娘,但工作照样能干,看来美国航班求务实而不讲面子。空嫂(年青人说是“空妈”)发给中国乘客一份中文繁体字的报纸,有几十页厚。据旁边的人介绍说是旧金山华人办的一份较为倾向台湾的报纸,但读这份报纸,并没有发现同大陆对着干的内容,除了一些在大陆上看不到使人不敢信以为真的奇闻外,就是演艺界名人的绯闻,再下来就是占用大量版面的各类广告。时光在流逝,两岸人们的心态也渐趋和平。我在飞机上翻来覆去看这份报纸,以排解长途旅行中的无聊,报上有一版栏目为“今古奇观”,有一篇署名为王璡的文章《胡适为陆小曼徐志摩做媒》,读起来颇有趣味,文章中说“最初是胡适看上了陆小曼,却因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这是我从未听到的说法,姑妄听之,未必可信,但也符合“文人无行”的说法。其中有一段使我相信的文字,且照录如下:
徐志摩与陆小曼都是再婚,非议颇多,胡适又出面请梁启超当了他们的证婚人,自己仍然担任这桩婚姻的介绍人。梁启超是徐志摩的恩师,也是徐志摩的忘年交,可因儿媳林徽因和徐志摩有过一段浪漫史,且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梁启超巴不得徐志摩早点再婚。
由于梁启超与徐志摩的婚恋观不同,在证婚词中,梁启超狠狠地骂了这对“新人”:“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如此痛快淋漓的臭骂当事人的证婚词,古往今来绝无仅有。此番臭骂来得痛快,来得真诚,非梁公不能有此臭骂,非对这对花鸳鸯不可生此臭骂,非此时此刻不能发此臭骂。作为证婚人发此臭骂,颇不近人情,但也事出有因,以梁公之高名,当时人也无奈地接受了此番臭骂。想来梁公当时并无文稿,而是即兴发言,所以流传的版本多种,但大意是一样的,语气也都是臭骂,所以不必去较真版本。徐志摩是少爷加风流才子,陆小曼是娇生惯养一身毛病的才女,二人结合在一起,过了风流浪漫的时段之后,太多的物质功利使二人的情感日渐淡漠,甚至出现了危机。如不是刚过三十六岁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亡,二人最终恐怕还是要走离婚的老路,看来梁公是看透了这对鸳鸯的毛病,所以才臭骂。徐志摩毕竟是一代才子,他是新月派诗人的重要人物,小时候读过他的新诗,至今还能背出他写给日本女人的几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从中可以真切感到诗人的浪漫与唯美。
如今看来梁启超在晚清至民国初期并不算是一流的书法家,用时下的话说是“业余作者”,但如今在拍卖会上他的遗作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成交价很高,想来这并不完全是出于他的书法价值,而是附加上了作为一代大学者的身份价值。我喜欢梁启超行楷书的温和儒雅,年青时曾有一段学过他的字,到现在我的行楷书还可看到他的影响。我更敬佩梁启超其人,他是大学者、真学者,真学者往往是诚实君子,诚实君子才会发出上述的臭骂。梁启超只活了五十六岁,却留下了一千四百万字的文章,且研究内容的学术涵盖面非常广泛,多有真知灼见,为近代史上的一位奇才,而书法对他来说是供休闲的末技。梁公发此臭骂而被世人谅解并接受,其要有三,一是梁公道德文章形成的权威性,如今时尚语叫做“公信力”;二是此番臭骂的客观性及明确的针对性,符合客观实际,才能被人所接受;三是梁公的一番真诚,一番热肠,以其诚与善来动人感人。
以梁公之臭骂推及书法的评论与批评,也须有此三者作支撑:一是评论家的专业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并非来自身居什么位置,头戴什么官帽,有什么大师之类的头衔,或来自媒体天花乱坠的炒作,而是来自长期以来用“学术修为”自我塑造成的在业内人心中的专业形象;二是评论的客观性和鲜明的针对性,以其评论的客观准确真实而被人所信服,所谓的“入木三分骂亦精”是也;三是评论的真诚与善意,要敢于直陈己见,敢于针贬时弊,而其出发点是善意的、有责任心而无私利的,不把人的恩怨带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不义气用事、感情用事。此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共同支撑起了评论的公信力。
评论家权威性与公信力是经过长期积累在专业内乃至社会上、历史上形成的专业形象,这种专业权威一但形成,他所说的话,他对古今书法作出的评说以及他的书法主张、创作理念,每每使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信任,这种信任并不能说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历史的参照而产生的专业信赖乃至对人的信赖。对于书法业内来说,历代书家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修养往往是分不开的,相互支撑共同塑造了书家的立体形象。基于这种历史的沿习,书法不同于其他学科或文艺门类,对创作水平高者往往人们对他所发出的论评信任度也高,手下有工夫,说话才能令人信服,如是单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其对书法的评论并不能让创作者完全信服。古代书法名家对书法的品评以及对书法现象评说的只言片语,往往成为历史的定论,被后人反复引用。而当下的一些书法博士生、硕士生为了拿毕业证而被动制造出来的形式规范的论文,一但拿到毕业证,其文章自己也不再去多看,更谈不上其文章在书法界、在历史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力。有些“网络写手”,并不缺乏对书法、对学术、对人的真诚,有时也能作出有价值的评论,但因其人缺乏长期积淀而成的权威,其发出的声音也很微弱,其论很难产生公信力,这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只有权威而不具有上述梁公的客观与真诚,其论同样难以产生公信力,如有些名家、大家为了面子、为了利益、为了“和谐”出面为一些仅仅属于一般书法爱好者的领导、老板、银行家等等写评论,闭着眼睛为他们吹捧、违心地把这些人描写成书法大家,评论者其人虽在业内具有权威性,而其论却不能产品生公信力,并且此类评论发表多了,其权威性就发生了动摇,因为他缺失了梁公的客观与真诚。有时他们所顾及的利益并不是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事业发展,希望有权或有钱的人为书法做点事,其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以丧失个人的专业信誉为代价,其付出也是沉重的,并且多数时候是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无法简单地用是非二字来对此行为作出评判,就如同一个女人为养活孩子而去卖身一样,无法用是非来评说。
评论的第二个要义是客观公正。这种客观公正除了需要第三个要义即真诚与善意作保证、也就是以高尚的人格作保证之外,其专业水平起到决定作用。这专业水平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深刻而辨证的思想,二是多元的专业乃至社会信息的拥有。所谓的客观公正,只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客观公正,任何评论都具有主观色彩,任何评论不可能人人都认为是公正的,但只要论据确凿,论述合乎逻辑,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便可使人信服。如梁公之评徐、陆这对鸳鸯蝴蝶,因其有证据确凿的“移情前科”,所以训斥他们要“痛自悔悟,重新作人”。在书法评论中真正作到客观公正是很难的,时下或有人手执所谓传统或文化的盾牌来痛骂新变,或有人高举所谓创新的旗帜而无视历史的传承,各执一端,以偏盖全,意气替代了学术,其论皆不能令人信服。有些评论只有结论的宣判,而无事实的依据和学术的分析作支撑,用著名文艺评论家廖奔的话说是“无思潮的论争,只有酷评”。廖奔指出当下书法评论的某些病态:
“有权有势者,给媒体一些好处,媒体就给他做专版,岂不知行内看这样的版面,都会对媒体嗤之以鼻。凡是组织的整版文章,大体没人看。有时看那文章,说的是那个作者吗?怎么说的和他的作品根本不一回事!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吹到天上去了。媒体上的书法最滥,丑字臭字充斥版面,会划个道道的都敢发表‘书法’作品,而吹捧文章也最多,因为这一领域里面无范式,无学院制约,不像美术有学院派,有标准和权威在。一些写字的,请名家到名胜之地吃饭、休闲、消费,好好伺候几天,让他过过上流生活,名家就肯出面为他写篇文章吹捧,权势者花费一点公款,名家就失去了贞操。这样的事,在金庸小说里江湖成名人物都不肯做。”(《文艺批评的战国时代》)
低俗的无原则的吹捧与无学术支撑的酷评是当下书法评论与批评的两极端现象,在种种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下,真正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客观公正并且有原创意义的书法评论很少很少。
评论的第三个要义是真诚与善意。梁公臭骂那对鸳鸯蝴蝶,被二人不情愿地接受,除了作为老师的权威,骂得合于事实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骂得真诚、骂得善意。真善美是国人认为的美好境界与高尚品格,没有人说自己是虚伪的、不怀好意的,但社会上乃至曾被人们视为净土的学术界如今也不乏虚伪。对于真诚与虚伪人们观其人、读其文时,不管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义正词严,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称,但中国人是讲中庸的,“看透不说透,都是好朋友”,于是大家都在这虚伪中生活,相安无事了,偶有一个说真话的人,反被视为异类,认为有“病”。沈鹏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沈鹏艺术馆藏品集》的“书后心语”中,写下了充满哲理又充满真诚的一段诗化的语言:
“……书法人选择书法,而书法只对那些善待它、有能力识别它的人感兴趣。书法精灵懂得怎样才是真爱,怎样才能促进它健康成长。书法精灵懂得无聊的吹捧、非分的颂扬实际是糟蹋,对于以它的名义为大众而实际为一己者采取不屑的态度。书法精灵受到伤害。它被疏远真善美,疏远人性,而这一切,常常是打着爱护它的旗号出现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沈鹏先生的“忧患意识”。我在《展览时代书法面面观》一文中,在论及当代书法的文化性反思时,提出最应反思的是当下书法界对文人风骨的淡漠及至失去,这种文人风骨中有着处世的真诚与作人的尊严。我们从梁公的此番臭骂中,也可看到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
(2012年载《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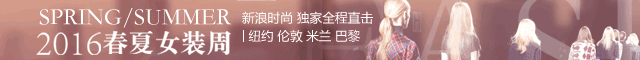











闂傚倸鍊搁崐鎼佸磹閹间礁纾瑰瀣捣閻棗銆掑锝呬壕濡ょ姷鍋為悧鐘汇€侀弴銏℃櫇闁逞屽墰婢规洟宕烽鐘碉紳婵炶揪缍€閸嬪倿骞嬪┑鍐╃€洪梺缁樏崢鏍崲閸℃稒鐓忛柛顐g箓閳ь剙鎲$粋宥夊箚瑜滃〒濠氭煏閸繈顎楀ù婊勭箘缁辨帞鎷犻懠顒€鈪甸梺闈涙缁€渚€鍩㈡惔銊ョ闁哄鍨熼崑鎾绘煥鐎c劋绨婚梺鐟版惈濡绂嶉幆褜娓婚柕鍫濇嚇椤庢绱掔紒妯忣亪锝炶箛鎾佹椽顢旈崟顓у敹闂佺懓鍚嬮悾顏堝垂婵犳艾鐭楅柛鏇ㄥ灡閳锋垿鏌涘☉姗堟敾缂佲偓閸愵喗瀚呴弶鍫氭櫇绾惧ジ鏌涚仦鍓р槈缂佹甯¢弻宥夋寠婢舵ɑ鈻堟繝娈垮枓閸嬫捇姊洪幐搴b槈閻庢凹鍓欓锝夋惞椤愩倗鐦堥梺姹囧灲濞佳勭閿曞倹鐓曢柕濞垮劤閸╋綁鏌熼鐐効妞わ箑缍婇弻鐔碱敋閸℃瑧鐦堝銈冨灪閻╊垶骞冨▎鎴斿亾閻㈢櫥褰掔嵁瀹ュ棔绻嗛柕鍫濇搐鍟搁梺绋款儐閻╊垶骞冨Ο琛℃斀閻庯綆鍋勯埀顒冨煐閵囧嫯绠涢幘璺侯杸闂佺粯鎸婚悷褔鍩€椤掑倹鍤€閻庢凹鍠楅弲璺何旈崨顓炴優闂佹悶鍎弬渚€宕戦幘鏂ユ灁闁割煈鍠楅悘宥夋⒑閻熺増鍟炲┑鐐诧躬閻涱噣宕橀纰辨綂闂侀潧鐗嗛幊搴g玻濞戞瑧绡€闁汇垽娼у瓭闂佸摜鍠愬妯哄祫闂佸搫娲㈤崹娲煕閹烘嚚褰掓晲閸噥妫勯梺鍛婃皑閹虫捇鍩為幋锔绘晩闁绘劦鍓氬В鍫ユ倵鐟欏嫭绀冪紒璇茬墕椤曪綁骞橀钘変汗闂佹眹鍨洪鏍g粙搴撴斀闁绘ê鐏氶弳鈺佲攽椤旇姤缍戦悡銈夋煏韫囧鈧洟鎮為崹顐犱簻闁瑰搫妫楁禍楣冩⒑缁嬪尅宸ユ繛灏栤偓宕囨殾婵炲樊浜滈悞娲煕閹扮數鍘涢柛銈冨€濆娲川婵犲孩鐣奸梺绋款儑閸嬬喖骞忚ぐ鎺撴櫢闁绘ê纾崢鎾绘偡濠婂嫮鐭掔€规洘绮撴俊姝岊槾缂佲偓婵犲洦鐓曢柍鈺佸暈缂傛碍銇勯埡浣哥骇缂佺粯绻冪换婵嬪磼濠婂喚鏆紓鍌欒閸嬫捇鏌涚仦鎯х劰闁衡偓娴犲鐓熸俊顖濐嚙缁茬粯銇勮箛锝呬簽闁汇儺浜畷婊嗩槻閻㈩垰鐖煎Λ浣瑰緞閹邦厾鍙嗗┑鐘绘涧濡厼危鐟欏嫮绠鹃柟鍐插槻閸熺娀寮ㄦ禒瀣挃闁搞儜鈧弸宥夋煥濠靛棙澶勬い顐f礋閺岀喖鎮滃鍡樼暥闂佹椿鍘介〃鍡樼┍婵犲浂鏁嶆慨姗嗗幗閸庢挾绱撴担椋庤窗闁革綇缍侀獮鍐ㄎ旈崘鈺佹瀭闂佸憡娲﹂崜娑㈡晬濮椻偓濮婃椽宕ㄦ繝鍐弳闂佹椿鍘虹欢姘跺箖濮椻偓楠炴帒螖娴e弶瀚奸梻浣呵圭换妤呭磻閹版澘围闁圭虎鍠楅悡娑㈡煕濞戝崬鏋ら柣顓熷笚椤ㄣ儵鎮欓崣澶樻&闂佽桨鐒﹂崝娆忕暦閵娾晛纾兼繛鎴炵懐濡啴姊虹拠鈥虫灀闁哄懐濮磋灋闁告劑鍔夊Σ鍫熶繆閵堝懎鏆炵€规洜鍠栧濠氬磼濞嗘劗銈板銈嗘肠閸涱喖搴婇梺鐟邦嚟婵潧鐣烽弻銉︾厱妞ゆ劗濮撮崝銈団偓瑙勬尫缁€渚€鈥﹂崸妤佸殝闂傚牊绋戦~宥夋⒑閸濆嫭鍣洪柟顔煎€垮濠氭晲閸涘倻鍠栧畷顐﹀礋椤掍胶妲梻鍌欑閹诧繝骞栭埡鍛煑闁告劦鐓堝ḿ鏍煣韫囨洘鍤€閻庡灚鐓¢弻锟犲炊閳轰椒绮堕梺鍐插槻椤︻垶鍩為幋锔藉€烽柟缁樺笧妤犲洨绱撴担绛嬪殭閻庢凹鍣e畷姘跺箳濡も偓闁卞洭鏌嶉崹娑欐珔濞存粓绠栭弻銊モ攽閸℃侗鈧鏌$€n剙鏋涢柡灞剧〒閳ь剨绲芥晶搴g矓椤曗偓閺岋紕浠﹂崜褎鍒涙繝纰夌磿閸忔﹢鐛€n亖鏀介柛銉戝嫷浠╅梻鍌欑劍閸撴碍绂嶉悙鍝勬瀬閻犲洤妯婂ḿ鏍煣韫囨挻璐$痪鎯у悑娣囧﹪顢涘杈ㄧ檨濠碘槅鍋侀崝鎴濐潖閾忓湱鐭欓柟绋垮瀹曟娊姊烘潪鐗堢グ妞ゆ泦鍥舵晪闁挎繂顦介弫鍐煏韫囧﹥娅呴柟顔藉灴濮婃椽宕ㄦ繝浣虹箒闂佹悶鍔屽畷顒勫煝閹捐鍗抽柕蹇婃閹锋椽姊洪崨濠勨槈闁挎洏鍊栭幈銊╁醇閵夛妇鍘遍柟鑲╄ˉ閳ь剝娅曞В鎰版⒑瀹曞洨甯涢柟鐟版搐椤曪絾绻濆顑┿劑鏌ㄩ弮鍥舵綈閻庢艾銈稿缁樻媴閸涘﹤鏆堢紓浣割儐閸ㄥ潡寮崘顔嘉ㄧ憸蹇涙儗閸℃稒鐓冪憸婊堝礈閻斿娼栨繛宸簼椤ュ牊绻涢幋鐐垫噧妞わ腹鏅濋埀顒€鍘滈崑鎾绘煥濠靛棛澧涚痪顓炵埣閺屾盯骞掗幘铏癁濡炪們鍨洪敃銏℃叏閳ь剟鏌eΟ纰辨殰缂佸崬寮剁换婵嬫偨闂堟稈鏋呭┑鐐板尃閸涱亜浜炬慨姗€妫跨花濠氬极閸喍绻嗛柕鍫濇噺閸f椽鏌嶉柨瀣伌闁哄矉缍侀幃銏㈢矙濞嗙偓顥嬪┑鐐差嚟婵即宕规禒瀣畺婵°倐鍋撴い顐g箞閹剝鎯旈姀顫婵犵數濮伴崹濂革綖婢跺⊕娲偄閻撳孩鐎梺鐟板⒔缁垶寮查幖浣圭叆闁绘洖鍊圭€氾拷闂傚倸鍊搁崐鎼佸磹閹间礁纾归柣鎴eГ閸ゅ嫰鏌涢幘鑼槮闁搞劍绻冮妵鍕冀椤愵澀绮剁紓浣插亾濠㈣泛顑勭换鍡涙煏閸繃鍣洪柛锝呮贡缁辨帡鎮╅棃娑掓瀰闂佸搫鐬奸崰鏍嵁閹达箑绠涢梻鍫熺⊕椤斿嫰姊绘担鍛婂暈濞e洦妞介敐鐐村緞閹邦儵锕傛煕閺囥劌鐏犵紒顐㈢Ч閺屾盯濡烽鍙ヨ檸闂佽宕樼粔顕€鎮烽幍铏暊闂佸壊鐓堥崰鎺楀磻閹捐鍐€妞ゆ劧绲芥惔濠傗攽閻愭潙鐏熼柛銊ユ贡缁鏁愭径瀣幗闂婎偄娲﹀褰掑Φ閻旇鐟扳堪閸曨厾鐓夊銈冨灪瀹€鎼佸极閹邦厼绶炲┑鐘插閸炴挳姊绘担绋挎倯濞存粈绮欏畷鏇熸綇閵娧屾祫濡炪倖鐗滈崑鐐哄煕閹达附鐓欓柤娴嬫櫅娴犳粓鏌涢弬璇测偓婵嬪蓟濞戞粎鐤€闁哄倸妫禍顏堝灳閺嶃劎绡€闁搞儴鍩栭弲顏堟⒑闁偛鑻晶瀵糕偓娈垮枦椤曆囧煡婢跺ň鏋庨柟閭﹀墮婵¤櫕淇婇悙顏勨偓鏍偋濡ゅ啰鐭欓柟杈惧瘜閺佸倿鏌ㄩ悤鍌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