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有两个观众,一是西方的大师,二是中国老百姓。二者之间差距太大了,如何适应?是人情的关联。我的画一是求美感,二是求意境,有了这二者我才动笔画。我不在乎像和漂亮,那时在农村,我有时画一天,高粱、玉米、野花等等,房东大嫂说很像,但我觉得感情不表达,认为没画好,是欺骗了她。我看过的画多矣,不能打动我的感情,我就不喜欢。
2、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视野窄。中国画近亲结婚,代代相因,越来越退化,甚至变得越来越猥琐。

3、我很幸运:出国前,是跟着潘天寿学的中国画,他是完全传统的,本人画得很好。后来我在巴黎学了3年,看遍了欧洲的艺术馆,知道西方艺术好在哪里;回来后结合国情,加以表现。我明白,传统的东西过去了,强调也没有用,鲁迅早就点出来了。回到传统是不可能的,抱着传统死路一条。但中国有大量画家不懂西方艺术,接受不了,有人连马蒂斯都骂,对西方艺术一律排斥打击,其实是束缚了自己,结果只会因袭古人,不会创新。中国画家凡是有点创新的,都学过西画。西方的大评论家对东方艺术不排斥,会欣赏。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香港举办了一个现代中国画展,媒体突出宣传两个重点主题:黄宾虹代表传统,吴冠中代表创新。他们评价我是叛逆的师承,“代表了一股巨大的超越传统的创新力量,令国画艺术焕然一新。”我在艺术上要求太严格了,考虑到百年以后的中国画前途,只是苦了自己……

4、画家走到艺术家的很少,大部分是画匠,可以发表作品,为了名利,忙于生存,已经不做学问了,像大家那样下苦功夫的人越来越少。

5、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感情有真假,有素质高低的不同,有人有感情,但表达不出思想。我现在更重视思想,把技术看得更轻,技术好不算什么,传不下什么。思想领先,题材、内容、境界全新。

6、人生只能有一次选择,我支持向自己认定的方向摸索,遇歧途也不大哭而归,错到底,作为前车之鉴。

7、整个社会都浮躁,刊物、报纸、书籍,打开看看,面目皆是浮躁;画廊济济,展览密集,与其说这是文化繁荣,不如说是为争饭碗而标新立异,哗众唬人,与有感而发的艺术创作之朴素心灵不可同日而语。

8、艺术发自心灵与灵感,心灵与灵感无处买卖,艺术家本无职业。

9、怀才就像怀孕。只要怀孕了不怕生不出孩子来,就怕怀不了孕。所以我天天在外面跑,就是希望怀孕。

10、笔墨等于零:脱离了画面,单独的线条、颜色都是零。笔墨不是程式化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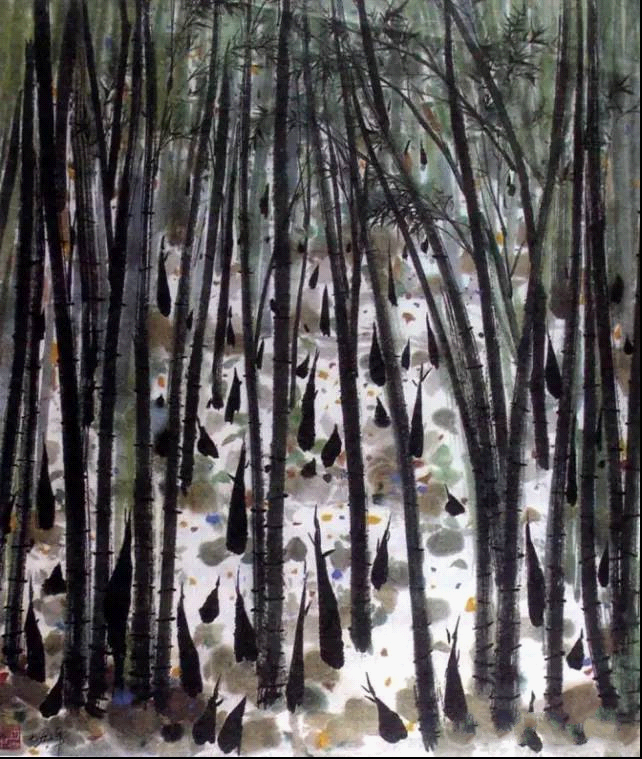
11、一个情字了得,年轻的我,抛弃浙江大学的工程学习,宁愿降班,转入了杭州艺专。从家庭的贫穷着眼,从我学习成绩的优异着眼,从谋生就业的严峻着眼,所有的亲友都竭力反对我这荒诞之举。我当然也顾虑自己的前程,但不幸而着魔,是神,是妖,她从此控制了我的生命,直至耄耋之年的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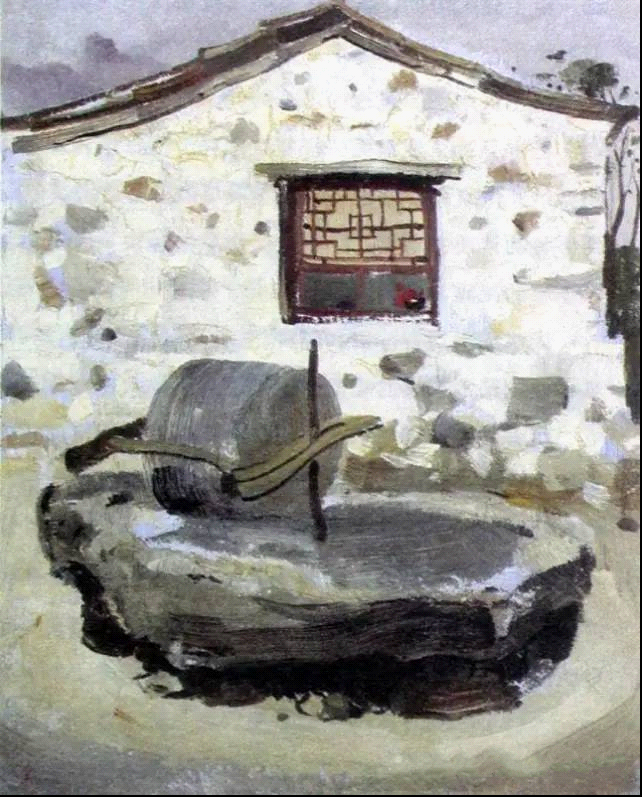
12、岁月流逝,留了回忆。一切的付出与坎坷都从创造中获得了解脱与回报:恋情被觉察的满足。恋情无边,发现真实与创造美,永远是诱惑科学家和艺术家忘我的动力。别人称颂他们的使命感,这使命感其实是感情的喷发或爆炸。

13、学艺之始,我崇拜古今中外的名家与名作,盲目的。岁月久了,识见广了,渐渐有了自己的识别力:名家不等于杰出者,名画未必是杰出之作。人死了,哪怕你皇亲国戚,唯作品是沟通古今中外的文脉。伪造了大量的废物欺世,后人统统以垃圾处理。我分析自己对名家与名作看法的转化因由,要害问题是着意于其情之真伪及情之素质,而对技法的精致或怪异已不再动心。情之传递是艺术的本质,一个情字了得。艺术的失落同步于感情的失落,我不信感情的终于消亡。

14、我写过一篇千字文,笔墨等于零: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文中主要谈创作规律,笔墨的发展无限,永远随思想感情之异而呈新形态。笔墨属技巧,技巧乃思想感情之奴仆,被奴役之技有时却成为创新之旗。石涛谓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明确反对以古人笔墨程式束缚了自家艺术,其实他早先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理念。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推翻成见,而成见之被推翻当缘于新实践、新成果的显现,历史上已多明鉴。

(文章来源:中国美术家网)

















